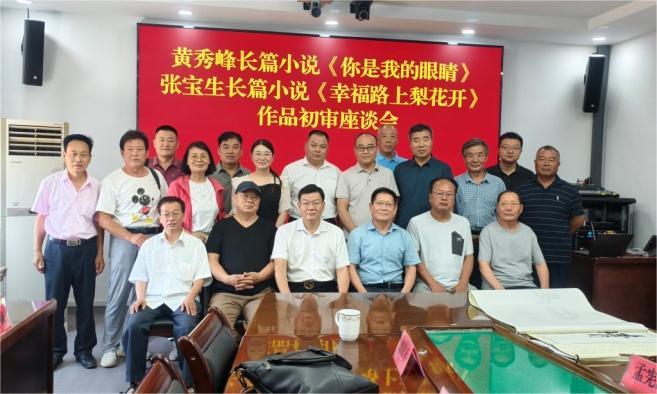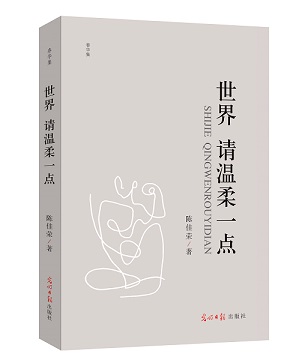一、序章:入梦的河床
泗水向西,将秋天锻成弯曲的钢;
银杏把黄金淬作冷硬的釉。
一个人站着,像楔入时光的钉子——
脚下落叶碎裂,是远去的蹄铁在响。
铁马冰河,就这样乘着深秋的风,
夜夜归来,潜入他清醒的白天,
化作笔底的沙沙、算珠的脆响,
以及凝视流水时,眼底那一片深沉的静。
那静,是吸纳雷霆后的真空。
你若望向张建鲁瞳孔的深井,
会打捞出1980年南疆凝冻的夜色——
那是铁马冰河最初叩击梦境的地方。
二、烽火:梦的种子
十八岁,田垄的墒情还藏在指甲缝里,
枪管的钢铁已烙进年轻的肩胛。
在生死薄如蝉翼的边境,
铁马冰河,不再是古诗里的遥想,
而是履带碾过冻土的轰鸣,
是潜伏时沁入骨髓的冰水。
偏在这绝地,梦的种子开始生根——
烟盒衬纸是疆场,蜡烛头是孤星。
张建鲁写堑壕边一夜苍白的野花,
写战友梦中反复泅渡的故乡河,
写炮火擦洗后,锐利如冰碛的星辰。
“为什么写?”许多年后,那声音自河底浮起:
“只为证明——在钢铁统治的领域里,
人的温度还在。枪膛是冷的,血是热的;
大地可以冻结,心仍能为美颤动。”
废墟中,曾寻得半本血泥胶着的笔记,
首页字迹晕散,宛如解冻的泪痕:
“当天空被撕成褴褛的布,
我看见,一只鸟,仍在用翅膀缝合。”
那不是诗,是命。
是铁马冰河入梦时,
灵魂为自己保存的火种。
三、商海:梦的拓疆
九十年代,大潮改道。
解冻的河床上挤满圈地的船。
张建鲁站在渡口,行囊里没有航海图,
只怀揣一颗被铁马冰河反复锻造过的心。
那夜夜入梦的凛冽,成了最硬的压舱石。
“用梦的温度,去触摸钢铁的逻辑。”
创办企业时,他在财务室隔壁,
亲手垒起车间的书屋。
《孙子兵法》的谋略与《国风》的吟唱,
并肩注视着冰凉的图纸与报表。
世纪之交,一次技术攻坚陷入冰封。
团队鏖战三昼夜,人人眼布血丝。
清晨,张建鲁推门而入,在氤氲的热气中忽然发问:
“可有人记得‘夜阑卧听风吹雨’的下一句?”
满室抬起困顿的眼。
他缓缓念出:“铁马冰河入梦来。
那闯入梦境的,从来不是恐惧,
是磨不掉的印记,化不开的责任。
我们眼前的难关,也只是另一条必须渡过的冰河。”
庆功宴上,一位白发工程师举杯微颤:
“张总,您那天念的不仅是诗,是胆气。
咱们缺的,正是这股从梦里带出来的、热腾腾的胆气。”
四、文舵:梦的篙桨
二零一四年,张建鲁执掌作家协会。
议论如风过隙:“一个商人,来搅动这方清浅的池塘?”
首次全体会议,他展开一幅精神舆图:
“文学不能仅是个人梦境的回响。
它应是篙,是桨,
是将铁马冰河般的个人记忆,
撑入时代江河的公共力量。”
《追寻岁月》定稿前夕,
他书房的灯,常是长夜里最后的孤星。
“白日,我丈量现实的疆土;
只有深夜,才允许自己抬头,
打捞从冰河深处浮起的、细碎的星光。”
二零二零年,疫情如寒潮再临。
大年初二,张建鲁写下《牵挂大武汉》。
这不是纸上的叹息,而是行动的号角——
他将散落的作家凝聚成一支文军。
有人不解:“作家也需要这样冲锋?”
他答得平静:“平常我们是造梦者,
此刻,我们必须是破冰者。”
五、幽隅:梦火照微
二零二五年春,张建鲁走向一片
常被视为精神荒原的土地——
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台下,是一张张被无形冰雪封冻的年轻脸庞。
他没有谈任何写作技巧,
只平静讲述:猫耳洞里噬骨的潮湿,
商海沉浮间如履薄冰的冷汗,
深夜里,面对稿纸如面对旷野的孤独。
“每个人心底,都曾有一条奔腾的河,
也可能,遭遇突如其来的严寒而冻结。
‘铁马冰河入梦来’——
那不仅是我的夜课,也可能成为你的。
文学不能替代太阳,
但或许,能递给你一截温暖的木头,
让你自己摩擦,让自己重新成为火种。”
后排,一个清瘦的年轻人慢慢举手,
声音仿佛来自冻土之下:
“老师……心好像被冻透了的人……
书里的那点火,还能烤得暖吗?”
张建鲁起身,穿过有形与无形的隔阂,
将一本边角温润的《活着》,
放入年轻人手中,
覆住那双冰冷微颤的指尖。
“书永远在等待。等待一颗心,
自己发出足够的热量,
去融化覆盖它的冰层。”
六、合鸣:梦的铸型
如今,标签繁多:作家、企业家、主席、教授……
但在知情者眼中,这不是头衔的累加,
而是同一尊精神器皿上,
经年累月、自然锻铸出的不同棱面。
军旅的铁马,商海的冰河,文学的梦境,
已在张建鲁生命的熔炉中反复煅烧,
交融淬炼,再难分离。
书房悬一幅自题联,墨色沉凝如铁: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实业报家国。”
宽大书案上,未竟的诗稿与待批的报表安然并处,
互证着一种生活的丰盈与完整。
窗台那盆从故乡移来的兰草,
不求花开,只以一身清矍的碧色,
静静吸收日月精华,
仿佛在沉淀另一种形式的、静默的铁马冰河。
七、渡口:梦即山河
辞别时,夕阳正将天边淬成一片壮丽的铁红,
缓缓沉入泗水。张建鲁即将驱车赶往学院——
今晚的课,主题正是“铁马冰河入梦来”。
引擎低鸣,他摇下车窗,暮风浩荡涌入。
“我这一生,”他顿了顿,
像在检索一部厚重的人生目录,
“无非是在反复验证一件事:
那些最凛冽的、叫作铁马冰河的事物,
当它们夜夜入梦,与你坦诚相对,
久而久之,竟成了你灵魂的筋骨。
你从此知道,温暖该有多暖,
坚持该如何坚持。”
车影渐融于苍茫暮色,如一滴墨汇入长河。
风从湖心吹来,带着深秋入骨的凉意。
但我知道,在那驶向讲堂的车厢里,
必有一团恒久的温暖。
战火锻打的瞳孔、商海磨砺的掌心、
与那支不肯休眠的笔,
正同频共振,鸣响一支属于这个时代的、
深沉而辽阔的和声:
最高的梦境,
从不是逃离现实的飞翔,
而是将最坚硬的现实——
包括那一路的铁马与冰河,
最终都化为梦境的本身。
让它夜夜入梦来,
铸成生命不可分割的、
沉重而有力的翅膀。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