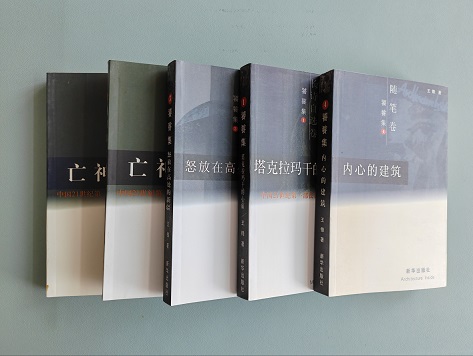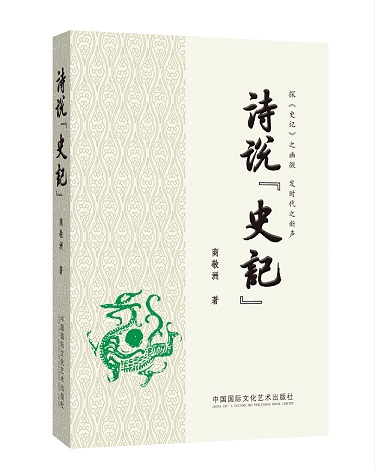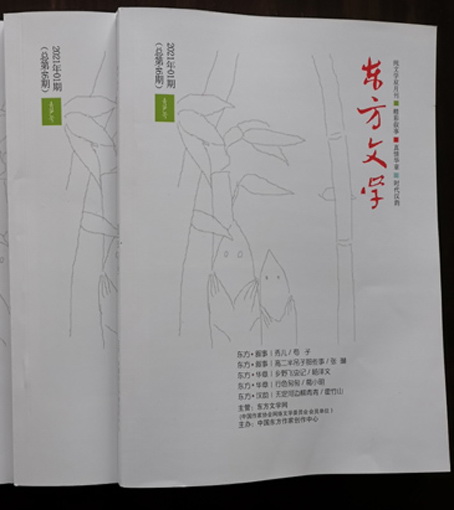我早就读过顺年的一些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顺年的小说深沉、凝重、洗练;他的散文细腻、隽永、感人;他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生动、意切、翔实。顺年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不仅具有丰厚、浓郁的文学美感,而且贴近生活,顺应时代,这些,都给我很深的印象。顺年还涉足影视,不仅发表过多部(集)影视剧本,他编剧的电视剧《军号声声》《我的梦》等都在中央电视台及省电视台播放并获奖。编剧的电影剧本《爬山虎》已在《前卫文艺》发表并得到军内多位将军的首肯,计划搬上银幕;编剧的电影剧本《你想不到》,已由上海电影局批准拍摄,现已进入修改和后期中;编剧的长篇电视剧(45)集《潍县集中营》(二人合编)已列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十四·五”规划》;顺年还创作过多部歌词,有的歌还被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放与推荐……而今,我又看到了顺年的诗集——《我心中的月亮》。顺年确是不失为一位文学(文艺)创作的多面手,取得创作的全面丰收,这在当今寂寞冷落的文坛,实属不易。
在顺年的诗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似乎没有浓烈的乡思乡愁,更没有苦难的状写和苦涩液汁的渗透,但是,顺年的诗中却充分体现了历史文化传统和个性的交融,体现了寻根意识和家园感的自觉追求。作为诗人,顺年在纯情的思绪中拍入美丽的田园风景线,又在广袤的时空背景下酿造出对家乡、对故人的深情。宁静、和谐的审美意义在诗人顺年大量的诗作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的童年》是写的自身,也是写的故乡,写的故乡的生活。诗人的童年是在牛背上“驮着”,是在小河里“淌着”,是在割草筐里“挎着”,是在水桶里“挑着”,是在犁沟里“走着”。精炼的诗句中“驮”、“淌”、“挎”、“挑”、“走”的选择和恰切运用,编织出了诗人也是农村孩子“人之初”的花环,由此可见诗人文学功底之坚实。
顺年带“故”字的几首诗,《故土》《故乡》《故人》,也无不跳跃着诗人欢快流畅的脉搏和热烈奔放的激情。他看到故乡,在顷刻间又变成了一个顽童,他走上故土,犹如投入母亲的怀抱,这难道不是诗人对人世间事理的体味和对故乡丰厚情愫的深切感悟吗?在诗人笔下,对故乡人,他不但“没有一句叹息”,也“没有半点彷徨”,坚定地踏着“厚厚的黄土地”,“充溢着对新生活的期盼与热望”,也充溢着诗人对新生活的无限激情。
乐观、明朗是顺年田园诗的基调和底色。
乐观、明朗也是顺年人生态度、审美意识和审美判断的基点。在《生活》《潇洒不是梦》等诗篇中,就抒发了他人生态度的豁达。额头的沟壑、鬓角的白霜、脚下的泥泞、都是人生的必由之路,他微笑着看待生活,直面人生的酸甜苦辣,诗人豪爽地直言:该笑就笑/该哭就哭/不要虚伪,不要作假,人生“有多解的方程式。”
还有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诗人在不少诗作中描绘和审视花谢、叶落、人老时,如《桃花谢了》《落叶》《日落》《朝阳与落日》《老树》《古槐》《老人与夕阳》等,是从那些“垂老”、“没落”、“沉沦”的客体现象中,发现的是成熟、丰收及新质和旧质的衔接与转换,非但没有叹息与悲伤,而是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中抒写一种坦诚、自信和充实。世间和自然界的人和事物,都没有永恒的存在和永恒的完美,也并非都是在保全自身中才能获得价值,而恰恰相反,价值有时是在自我残缺甚至是在自我消亡中才能得到最充分最完美的体现。
《桃花谢了》仅仅六句诗,诗人却描绘出了一个客体生命自身的演变转化过程和希望对新生的追求。花谢了,似乎是终结,但却在“绿”中获得了新生和开始,而且悄悄地“迈向成熟的果实”。花的消亡,换来了绿,换来了果实,就愈发显出生命的充实。这是诗人通过对自然现象的描写着意挖掘出其中蕴含着的对人生、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人思想的启迪。
写日落,不少诗人往往都会寄托着悲伤。但顺年的《落日》,却充满着希望和辉煌。这种情结和思绪,这种对事物也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在《朝阳与落日》中更有进一步的的表现。诗人赞美朝阳,因为朝阳是新生是希望;诗人也赞美落日,因为落日不仅是悲壮,而是对事业的完成。面对朝阳的挑战,“落日却不言语/因为它拥有的是整个世界”。日头不能常晌午,在这民谚中就蕴含着哲理。顺年的《朝阳与落日》《落日》也是这一哲理的体现,但作为诗,它还追求着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极高极丰富的,也是诗人在历经沧桑之后才领悟到的。
顺年的哲理思考在其长诗《潍河之歌》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首诗激情洋溢,气势磅礴,诗人以潍河为具象,融入了自己的丰富人生体验,写潍河,写人生,通篇蕴含着深刻的象征意义。在这首长诗中,诗人有对潍河的赞颂,也有对自身的激励;有对潍河自然生存状态的描述,也有对潍河拟人化的感情的宣泄。这就是这首诗具有耐人寻味的多样性。《潍河之歌》长诗的开头第一句“你是山里的孩子”,怀着对山的依恋之情,“迈开了离别那山的脚步”,继而写环境的变化使你“忘形”,“变得高傲变得放荡不羁”,继而再写经过痛苦的磨炼后“接受了批评采纳了忠告领悟了教诲,认清了未来的归宿应是浩瀚的大海”,要“在追寻大海的路上渡过平淡的一生”,诗的结尾是“你也是大海”。诗人把潍河自然存在状态的历史和现实描绘的惟妙惟肖又丝丝入扣、一波三折地抒发着对人生历程的咏叹。
顺年的咏物诗亦别具特点,往往从细微处着笔,寄予着一定的含意,诗句酣畅流利,隽永谐美。如《冰花》,即取其直面酷冬严寒的勇气,歌颂其“没有娇柔”,“没有造作”的特点。《岸柳》则以柳那柔美的自然属性延伸出情人间的恋情。《春风·春雨·樱花》将自然景物融为一体,共同营造出了一个童话世界,显得新颖别致。《小溪》则从冰雪严寒锁不住它的细流,高山峻岭挟不住他豪情壮志的特点,令人顿悟出人生之路应该怎样走的真谛。
在顺年的诗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爱情诗。顺年的爱情诗构思新颖,感情充沛,格调高雅,爱的向往爱的真挚爱的追求在《第一次约会》《初恋》《致F君》《渴望你再来》《等你》《思念》《那片草地》《默默地相思》中得到了尽情的描绘。顺年的爱情诗读来无不感到情真意切和甜美的享受。本部诗集《我心中的月亮》,是诗人独具匠心的力作,作者又将其冠以书名,可见其用心良苦。
当然,在顺年的诗作中,有些亦使人感到缺乏新意,有的诗显得粗疏了些,在对人生的观察、体验、思考上也有待进一步向更深处挖掘。
艺无止境。顺年的诗曾发表在国内多家文学期刊和报纸文学副刊,特别令人感到高兴地是,顺年的诗歌《乡村故事》还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确实不易的,望再接再厉,一路繁花,继续攀登诗坛高峰。我期待着,期待着顺年更多、更好、更美的诗作问世。
任孚先,山东莱芜人,中共党员,著名文学评论家,一级文学创作(正教授级),曾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是山东文学界的重要学术带头人。
一、教育背景
自幼受家庭文化熏陶,广泛阅读古典名著等,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基础。
其教育经历是: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师从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等学者,在校期间即在《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谈〈青春之歌〉》《论〈红旗谱〉》等学术文章,在同学中崭露头角。
二、学术研究
研究领域涉及文学理论、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多领域,尤其擅长以现代视角解读古典名著。其《聊斋志异艺术论》,从人性美、人情美角度重新阐释这部经典,强调蒲松龄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贡献,并提出当代作家应继承这一精神。
著作有《片羽集》《任孚先文艺论集》《聊斋志异艺术论》《任孚先序跋集》等专著,主编《齐鲁文化大辞典》《中外文艺评论小辞典》等工具书,填补多项学术空白。
在区域文学研究方面,其《山东解放区文学概观》系统梳理了山东解放区文学脉络,获山东省社科二等奖、全国解放区文学一等奖;《现代诗百首赏析》以细腻解读推动现代诗歌研究,获泰山文艺奖。
三、创办文学期刊
创办山东省唯一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家》(后更名为《文学世界》《新世纪文学选刊》),任社长、主编期间刊发大量前沿理论文章,推动了全国文学批评发展。并以 其“理论性、当代性、探索性” 为办刊宗旨,培养了大批文学新人。
四、兼任社会职务
担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后,积极推动山东文学与全国文坛的交流,尤其关注本土作家成长,为李存葆、王润滋等作家撰写评论,助力其创作定位。同时还曾兼任《山东文学》编辑、省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等职,长期参与山东省文学界的决策与管理。
五、文学理念与批评风格
主张文学批评的参入意识,强调文学批评应主动介入创作实践,反对脱离现实的纯理论研究。他在《〈山东文学评论选〉序》中强调,批评家需 要的是“接近现实,参与文学自身的变革”。
他还主张文学批评家要开放视野:将山东作家置于全国文学背景下考察考量,既肯定齐鲁文学赋予的厚重底蕴,也指出其局限性。例如,他分析刘知侠(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作者)的军事文学创作时,既赞扬其史诗性,也探讨其题材拓展的空间。
六、社会影响与荣誉
长期关心山东文学发展,担任 “全国首届吴伯箫散文大奖” 评委,助力地方文学事业。
获荣誉奖项有:《片羽集》获山东省社会科学奖、《现代诗百首赏析》获泰山文艺奖,其学术成就被载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等权威文献。
学界评价:被称为 “山东文学界的思想旗帜”,其批评风格兼具严谨性与亲和力,既具有学院派的深度,又能贴近创作实际,深受作家与读者尊重。
任孚先的学术生涯贯穿新中国文学发展全程,其研究与批评不仅为山东文学奠定理论基石,也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提供了区域视角的范例。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