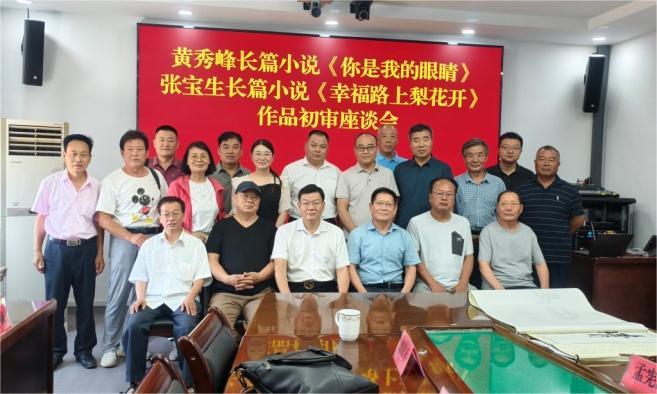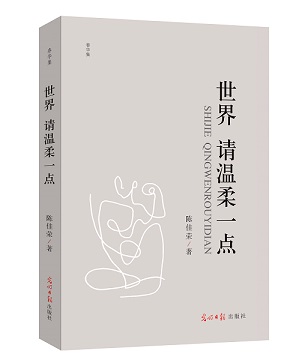年终盘点是一种习惯,也有必要,但文学不是按年头突变的。有时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出端倪。但今年仍有几点给我印象深刻。
一是,我早指出过数字化时代的阅读分化问题,各类阅读井水不犯河水,这情况已有几年了,到近年尤盛。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类型小说,吸引了大量青年读者,类型化创作不但在网上也在图书市场上强势,比如悬疑,推理,玄幻,盗墓,穿越,后宫等等,传统文学读者的一些人也被拉过去了,整体上有减无增。这可能是网络和消费时代的普遍现实。这里也有好作品。但我认为,总体上看,这在科技手段上是进步了,在媒体传输甚至文明程度上提高了,但是在文化精神上并没有多大进步。主要是,快感阅读取代了审美阅读,消费性游戏性阅读所占份额过大,于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怎样增大魅力,扩大对读者的影响,是个重要问题。一个民族的文学必须有它的“塔尖”,在纯文学领域,如何创新以适应媒体化时代的读者,能以其原创性,深刻性,切中当代社会的精神,直指人心,就是突出问题。
目前传统文学中数量与质量不平衡的问题仍非常突出,所以文学界需要保护或维护有真正人文精神的作品,需要大量扶植和引导具有鲜明深厚的正面精神价值的作品。这样才能在热闹的图书市场中,树起精神的标高和塔尖,否则会被一些表面的繁荣所遮蔽。
二是,官场小说的流行或称为泛滥,成为一个重要现象,基本占据了大众阅读的重要空间。一方面,要看到,这是社会心理的反映,是反腐倡廉的社会需求刺激了官场小说的生长。但是官场小说的创作也存在很多问题,有些作品成为升官秘笈或腐败展览会,有些热销书不是以思想艺术力量取胜,而是倾向于对官场的窥视,倾向于娱乐、消遣,缺乏精神力量和充沛的正气。如果说《苍黄》写得较好些,那是把官场作为平台,写了人性,写了日常,写了文化。现在官场小说实际上是最大的“类型化”,这种势头不利于文学表现广阔多样有机联系的当代生活。
三是,总体上看,2009年的文学,是平稳地波澜不惊地沿着前几年的轨道继续前行,出现了一些好的作品。在长篇上,比如阿来的《格萨尔王》、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张者的《老风口》、高建群的《大平原》、苏童的《河岸》、刘醒龙的《天行者》、周大新的《预警》、王小鹰的《长街行》、钟求是的《零年代》、阿耐的《大江东去》、凌行正的《九号干休所》、王刚的《福布斯咒语》、里快的《狗祭》、樟叶的《晚春》、秦岭的《皇粮钟》、翟岱海的《辛家湾》、廖齐的《茶道无道》等等。纪实文学《解放战争》也写得很不错。去年海外华人的创作格外引人注意,取得很大的成绩,是他们的构思更精,心更沉静,汉语叙事能力更好?这是需要研究的。 回顾这一整年的创作,原创性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在很多作品中,精妙的细节、饱满的人物,有启迪力的思想,深邃的意境仍然匮乏。
张颐武:三足鼎立的结构仍然稳固清晰
《小团圆》的出版带有突破性,使读者对张爱玲创作生涯的理解有了新的深化。
传统作家值得关切的,仍然是一线的主流作家,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莫言的《蛙》都是有趣的新作品,保持了他们的创作水准,声誉很高。他们的创作已经相对职业化了,跟西方的职业作家状态很像,两三年推出一部作品,轻易不失手,但是有重大突破也难。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创作也基本稳定,但尚未进入中国作家的“第一梯队”。70年代作家也做了努力,但是在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的夹缝中尴尬生存,没有开拓出新的空间,呈现出萎缩的状态。80后作家仍占据着青春文学的市场。
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三足鼎立的结构仍然稳固清晰。《小时代》的第二部,受到了青少年读者的热捧,现在郭敬明和他的团队在青春文学中还是很有优势。
去年网络文学声势比前几年更为壮大,包括榕树下“复活”、重要的文学网站都归到盛大文学的旗下,一系列的活动使公众对网络文学有了更重要的认识,但是网络文学转化为纸质出版后,发行量明显不敌点击率。另外,《潜伏》、《蜗居》等影视文学作品继续保持了强劲的势头;应用性的图书,比如《杜拉拉升职记》以及官场小说,都是稳中放大。总体上看,虚构文学发展不错。
孟繁华:文学之花依然盛开
2009年,对文学现状的整体判断依然是毁誉参半莫衷一是。但“三分天下”说似乎引起了一阵波澜:网络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冲击被认为是一大转折。但事实远没有描述的那般可怕。
2009年长篇小说有两个“事件”性作品:一是张爱玲《小团圆》的出版,一是《废都》的再版。《小团圆》将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推向了2009年的高潮。张爱玲在坊间构建的神话持续多年,在即将消歇时《小团圆》犹如一针强心剂,重新起死回生。《废都》无论以哪种形式重新出版,都是一个重要的事件,都会引起读者和文学界极大的兴趣和关注。1990年代是社会大转型的年代,道德化标准还是文学批评的标准之一。《废都》中性描写的不合时宜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这部作品的全部丰富性才有可能被重新认识。
在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新历史主义”、“祛历史化”和反映当下生活的作品表达多元现代性的冲突,仍然是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主体,它没有“断裂式”地另起炉灶,而是接续和发展了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方向。
长篇小说写人的命运,大多与国家民族叙事有关。宗璞《西征记》对战争与人性的深刻把握,使之成为表达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作品;高建群的《大平原》是一部叙述家族史的小说,也是一部向乡土中国女性致敬的小说。《皇粮钟》再次证实了秦岭对历史的记忆和书写热望;当代文学对重大历史事件缺乏持久关注的耐心,李森祥、薛荣的《送瘟神》对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防治血吸虫病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书写,显示了两位作家的眼光;李师江的《幸福之州》显示了年轻作家的艺术想象能力,也体现了70后作家文学探索的努力和态度;阿来以《格萨尔王》参与到全球出版工程“重述神话”;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再现了20年代旧武汉的生活场景;老作家张惟的《血色黎明》以闽西苏区作为主要背景,以闽籍出身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主要人物,以革命历史事实作为基本材料,生动地叙述了自1919年到抗战胜利前夕,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书写历史是长篇小说的一个传统,今后仍然会产生大量的作品。2009年更值得注意的是一部“祛历史化”作品的出现,这就是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小说的核心部分,是对现代人内心秘密的揭示,这个内心秘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近年来的小说创作,与当代生活的关系在逐渐恢复。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生活是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最重要的资源。有思想能力的作家总会在当下生活中找到自己创作的灵感。阿来在2009年出版了他的《空山》系列第三部,表达了经济大潮冲击下藏区价值观念的变化及作家的忧虑。刘醒龙的《天行者》关注的是教育的底层;周大新的《预警》具有强烈的警示的意味和意义;张学东的《超低空滑翔》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反映民航生活题材特殊的作品,它的专业性决定了没有体验是无从下笔的。
2009年,反映当代生活、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当下公共事务的作品,最有影响的应该是曹征路的《问苍茫》。对“官场”的书写,应该是新时期以来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被坊间称为“官场小说”“二王”的王跃文、王晓方分别出版了《苍黄》和《公务员笔记》。关仁山的《官员生活》的发表,为这一文学现象添加了新的想象和理解。关仁山将这部小说命名为“官员生活”本身,似乎是有意为之的客观描述,同时也有一种同情、理解的意味蕴涵其间。这是一个“多元现代性”时代。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在《官员生活》中我们发现:小说的主要矛盾并不仅仅来自权力争夺、权钱交易或情色演绎。
2009年,长篇小说创作的全部丰富性不可能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得到呈现,但我可以断言的是:文学之花依然盛开。
贺绍俊:突破处理中国经验的局限性很重要
我专门提一部大家都不太关注的作品:加拿大华人作家李彦译写的《红浮萍》。为什么特别看重这部作品?好多年以前我就盼望看这部小说。因为当时我看到有新闻说,李彦的《红浮萍》获得加拿大最佳图书提名奖,我很惊奇,这是他们主流文学的一个奖项。虽然80年代有很多中国人出国留学定居写作,还涌现出一些在内地非常有影响的海外作家,但他们只能对中国文学有影响,很难进入当地主流。这条新闻引起我的兴趣。
《红浮萍》英文名是《红土地的女人们》,写以女人为主角的一个家族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遭遇。李彦自己介绍说是译写,还有重写的意思。这部小说,放在中文小说里不会很出众,但李彦的长处是双语写作,她精通英语,把中国故事用英语表达,完全符合英语语言思维习惯。她在国外生活,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回头看经历过的这段历史,通过西方文化思维的调整,可能比较超脱,不会像我们那样急功近利,过于实事求是,在精神价值和文化价值上有所超越。同样的中国故事,用英语表达出来,就容易被西方主流文学认可。看她中文本时,发现她在回头处理她的经验时,其态度从容多了,更多地会在语言的典雅性上下功夫。这恰好是我们讲这段故事时最缺乏的。
李彦的写作,经过双语转化,摆脱了我们的思维习惯。这种信息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我们的作家未必掌握外语或到国外生活,但重要的是,怎么突破我们处理中国经验的局限性?李彦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盛世之争和衰世之争是去年重要的文学现象。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也带来了对文学60年总结的话题,其中引出了很有意思的争议,就是关于盛世文学与衰世文学的争议。这个讨论虽然只是在一些人中间展开,它的影响却是长久的、深远的。在这场争议中,有一个重要问题被我们忽视,却是以后需要解决的——我们怎样看待文学的自由。长期以来,西方有一种质疑,经常要问中国的作家:你们现在能否自由地写作?你很快就会发现,一些中国作家误会这质疑落脚点是在外部条件,于是会辩解我们没有那么多约束,这是最大的误解。从中外历史来看,优秀伟大的作品,并不是在宽松的环境中写出来的,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内在的精神自由。中国文学缺乏内在的自由。
陈晓明:长篇小说大年
相比2008年而言,去年可称为长篇小说大年,出现了几部很有分量的作品。我关注到的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能够把有汉语言品质的文体表达充分,有很强的本土文学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刘震云在西方现代文学的背景上看到现代汉语的意味,越写越往心里走去。刘震云写了很多人物,不断地写他人,但都和社会历史和农村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很了不起。他的小说就是家长里短,写农村的三教九流的生活,写农民怎么找说心里话的人,农民的现代意识是怎么崛起的。在这小说中,现代意识和传统千丝万缕联系在一起,又有作者独立的思考。书写是全新的,土得掉渣,但却是以中国方式呈现的。
在苏童的《河岸》中,我没有找到令人惊叹的、和他的才华名气相称的东西,《河岸》重新回到先锋派,回归到一种重新的出发。虽然是对历史重新书写,但有个人对自我历史的寻找和失败,整个叙事有节奏感自由感,人物活在语言的飞扬中。苏童的语言依然瑰丽纯净。
我也注意到一些作品是非常独到的,宁肯的《目光之城》就做了很多探索和文本实验,一方面是写西藏生活,一方面是对生活的敬畏和反思。另外,还想提到虹影的《好玩女花》,据说可以作为《饥饿的女儿》的下部,这部作品可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因为太写实了,写到爱和婚姻的巨大破碎,是对家庭伦理、对身体、对女人命运最彻底的审视,虹影把小说经验推到极致。我们不必忙着评判作品的好和坏,但是对极端的文学经验怎么看待值得讨论。我也注意到虹影的小说叙述显得非常老练,语言干净利落,她是颇为彻底的小说家,彻底到完全地写作她自身的经历。
莫言的《蛙》是非常有分量的作品。不是大作家一定会出大作品,但是莫言的每一部作品都很厚重。“我姑姑”作为主人公,显示了莫言关注现实的态度。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影响了中国几代人,文学作品中有一些表现,但像莫言这么全面表现计划生育的作品没有,反映中华民族在这样的经历中留下烙印的作品值得重视。
艾伟的《风和日丽》发表在《收获》的第三、四期,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写到对革命的反思,显示出作家的思考变得成熟大气。
还有一部作品必须要谈:赵瑜的《寻找黛莉》。作品带给我最大的震撼是,写出了大家庭在现代历史中的被破坏。山西的经济和文化在中国现代史上非常重要,从近代进入现代,则开始衰败。这部作品通过寻找黛莉的身世,写出她背后的遭际,家族和阶级的覆灭,以及和她家族相关的山西那些大家族被破坏的命运。写得非常棒。
张翎的《金山》是非常大气的作品,小说叙事在一个时代的两个时空里自由变化。中国的家族小说非常发达,经历这些之后再关注个人,是漫长而必要的基础。阎连科的《我与父辈》以他非常冷静的平易的方式写出和父亲的关系。阿来的《格萨尔王》在“重述神话”的作品中是出色的,有人没读就污蔑是旅游小说是荒谬的。
综合看来,作家回到本土的意识更加明确,更加深刻;先锋文学的经验在《河岸》这里得到更有力的提升;中国作家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大气,艺术水准有很鲜明的提高。作家越来越具有个性化的特点,这表明作家本身也在寻求变化,显示了他们的勇气和觉悟。
李敬泽:海外华人作家占据重要位置
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像《金山》、《一句顶一万句》、《格萨尔王》等都是比较突出的作品。在去年,我们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华语写作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大陆、港台和海外的作家,共同参与了文化生活,去年广受关注的几本集子,主要是港台作家的,张大春、梁文道、龙应台。
现在出现了一批“新海外华文作家”,《人民文学》在第12期专门为此发了一个专号,这包括旅美的严歌苓、袁劲梅、陈谦,旅英的虹影,写出《金山》的张翎在加拿大,还有加拿大的陈河,新加坡的张会雯等。过去我们谈到当代文学,主要是大陆文学,其他从港台到海外,都作为当代文学的边缘,他们可能是接续着现代文学的谱系和传统,但和大陆的当代文学基本上是分头发展,没什么关系。但现在不一样了,随着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人、大陆人在世界范围内迁徙,一些人在海外开始写作,他们的背景和文学经验都是从大陆带过去的,在跨国、跨文化、跨语际的处境中,他们对当代文学做出回应,带来了很多新的主题、观点、经验和气象。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力扩展。也许今后我们再谈当代文学,就不能仅仅谈大陆,还要谈港台和海外,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场域。这一现象并不是始于2009年,但在这一年变得特别明显。
白烨:命运与时运的交响回旋
长篇小说作为文学创作的指标性体式,越来越为文坛内外所看重,但要在普遍阅读的基础上做出基本评估,却也越来越困难。究其原因,是出书的品种太多,数量太大。从传统批评的角度来看,长篇小说领域虽然越来越数量激增,面目不清,但其基本的构成还是两大类的写作,即以职业或专业作家为主的传统型或靠近传统型的写作,以业余或网络作家为主的类型化或靠近类型化的写作。在作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传统型长篇小说以求在文坛内外留有一定印象为旨归,而类型化长篇小说以求在市场上获取最大影响为目标,这样一种隐性的动机区别,使得人们更为关注传统型长篇小说,并把它看做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水准的更高代表。
就传统型长篇创作的情形来看,2009年的长篇小说在数量持续增长的同时,质量上也在不断攀升,在前行的平稳与收获的平实之中,自有一种内在的丰硕。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2009年的长篇小说中,不同题材的领域里,都有货真价实的佳作力构,而且都以自己独辟蹊径的艺术探掘,让人读时欲罢不能,读后回味悠长。还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涉及什么题材,描画什么人物,许多作家都强化了对于人的个性的索解,对于人的命运的追踪,并在个人与社会,人生与时代的密切勾连中,探悉彼此之间相互制约又相互改变的生态与实情,使得命运走向与时代走势的交响回旋,成为了凸显于2009年长篇小说的主导性旋律。
涉及到现实与变革的作品,在2009年中为数不少,这既是改革开放已走过整整30个年头,一些有心的作家有意要为这个新时期以来的30年的辉煌巨变描影造形,更为主要的却是创作中一直存在的写实倾向,在2009年间又有了别求新声的切实成果。比较之下,这一类作品中,值得人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阿耐的《大江东去》,曹征路的《问苍茫》,王小鹰的《长街行》,刘醒龙的《天行者》。
凸显个人的视角关护个性的成长,以探究命运的方式关注个体的生存,就成了许多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一再呈现的主题。徐贵祥的《四面八方》中,人物的悲情遭际揭示得让人触目惊心。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中主人公水上灯的人生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性格的悲剧。苏童的《河岸》中异常的灰色记忆与隐秘的人生体验,将少年的青春骚动与成长困惑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把社会的无情与政治的冷酷,个人的卑微与生命的顽强,都揭现得无以复加。
莫言的小说《蛙》,异乎寻常地回到了现实性的叙事,并经由“姑姑”这样一个典型人物,讲述了一个乡村女医生的性格变异,“姑姑”的心理矛盾,当然也折射着时代与历史的矛盾。
对于乡土题材作品,2009年间一些实力派作家作出了自己饶有新意的探悉,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这种写作的一个典型代表。高建群的《大平原》、成一的《茶道青红》都有其独特之处。
眼下的官场小说领域,大多没有走出模写现实的窠臼。2009年,这种状况有了一定的改观,这得力于王晓方的《公务员笔记》、王跃文的《苍黄》、张效友的《国家誓言》和周大新的《预警》等几部力作的联袂出现与明显出新。02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