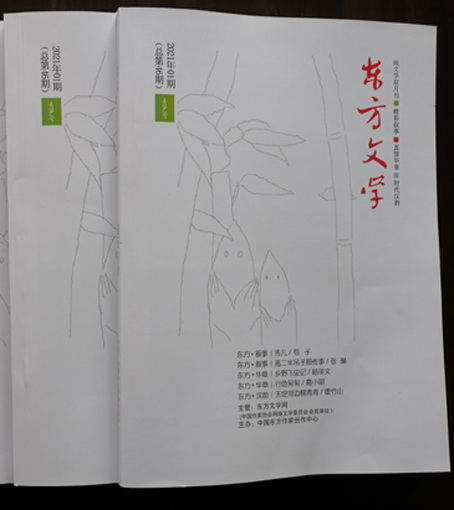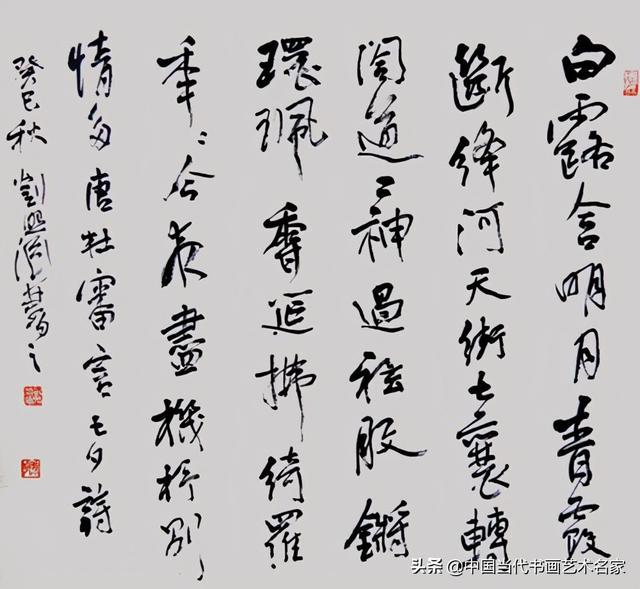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
|
|
秦淮河上寻桨声
最早对秦淮河的认识,缘于唐代杜牧的《泊秦淮》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雾霭如烟,月蒙蒙,夜蒙蒙,酒肆飞歌,人家热闹,商女如花……从此,在我的印象中,秦淮河与风月,与商女、人家、诗人是裹挟在一块的。 当时的我没有能力走近秦淮河,只能是心生些无端的遐想。想什么呢?想秦淮河的风月,历经六朝累下来是不是可以垒成一摞诗册了?想有谁可以测知秦淮河里究竟溶了商女胭脂红多还是溶了商女的相思泪更多?想秦淮人家是谁?是酒家、船家、商家、女人家?是酒家的花雕芬芳,是船家的轻舟载月,是商家的挥金如土,是女人家的袅袅婷亭?想是秦淮河风流还是来到秦淮河的诗人风流?是秦淮河的风流诱发了诗人的风流,还是诗人的风流赋予了秦淮河的风流?到过秦淮河的人说,在秦淮河诗境与环境曼妙无比——诗歌中可以读出秦淮河,秦淮河可以流出诗歌。 我想象的秦淮河,两岸的酒家肯定是要有的,软软的吴歌也肯定是要有的,即便是艳俗的女子也可以是有的,而每个酒家门前肯定也飘逸着一方旌旗或是几枚灯笼,打着诱人的“秦淮人家”字样,吸引着天下来客;临河的窗边最好有一扉窗开着,窗台上吊一盏小灯,供着一盆兰花或茶花,或倚着一个婉约的江南女子,如果没有女子倚窗,则要有吴歌从窗里飘逸出来,迷得游船的才子、公子们船舱探头,引颈项觅美人。而秦淮河的水呢,必定是清澈见底,甚至可见鱼虾追逐,船从如镜的水面划过,划出一道清波,清波在逶迤的灯光下闪烁着片片磷光;天上有一轮孤月随着船走,船窗里有三两个知已男女,或抚琴或轻歌,或饮酒或品茗,或叙情或抒怀,尽说些风花雪月之事。如果是冬天则要有一炉暖炭煮着黄酒,如果是夏天则要有一把绢丝的扇摇着凉风,如果是春天就遐想“无风自婀娜”的王献之诗中的桃叶姑娘,如果是秋天就戏说来江南贡院考试的才子唐伯虎的风流韵事…… 后来,我读大学时,读到了朱自清、俞平伯两位散文大师的同题美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对秦淮河有了新的感悟。两位大师因为生活经历和对事物感悟的角度不同,出来的文章或重于抒情或偏于状景,伯仲难分,均是千秋文章。这时的秦淮河,已然没了六朝的历史味的古韵,但仍有商女的歌声从“生涩的歌喉里机械的发出”。朱、俞是性情中人,更是道德中人,显然不适应这种缺乏情韵的歌声,他们宁愿在灯与月交溶的秦淮河静静的一隅“静听那汩——汩的桨声”……于是,秦淮河的风月在我心中演变成了“汩汩的桨声”。 2005年农历大雪的一天,我走近秦淮河。时值寒冬,却人流如织。秦淮河窄窄的,不过百米,两岸灯火如炬,迷离闪烁,旧唐诗流淌的风韵被放大有些变形,感觉上更似一位珠光宝气的女子。这热烈的场景令我一时竟不能适应。我心想:秦淮河可以有商女有人家,但秦淮河不应该是如此艳俗的呀? 显然,我要失望了。把秦淮河定格于美好想象的诗歌与传说中,只会是如同朱自清一样的结局了——“心里充满了幻灭的情思”。21世纪的市场经济,商业运作古文化,秦淮河的商味浓郁得像粘稠的蜜,现代、时尚的霓虹灯五光十色,加之形色匆匆的人群、南腔北调的人语,鼓惑得秦淮河的清韵全然无了踪影。或许,秦淮河的唐诗宋词的妙韵全部回到诗卷中去,回到历史中去了。这日,天寒地冻,我四处寻觅也没有寻觅到曾经载过朱、俞的那种带桨的“七板子”船,因此,我放弃了游船的想法,我预见上了船去必定也感受不到杜牧的诗韵,感受不到朱、俞笔下的那感动人心的“汩汩的桨声”。 其实,浮躁的是人心。秦淮河始终是厚重的,她沉淀了层层叠叠的历史,流逝了年年岁岁的时光,而且,还将继续把历史沉淀,把时光溶解,直到永远。秦淮河始终是静谧的,她历经千秋岁月,早已看惯了风花雪月、刀光剑影,看惯了朝野更迭、聚合离散,看惯了春风扬柳、冰霜残梅,也早就听惯了商女们的歌舞升平,习惯了商女们的爱恨情仇。秦淮河始终是自然的,她为城市承载了过多的奢侈,包容了过多的繁华,可这奢侈与繁华是人类给予她的呀,应该返朴的是人类,是搅了秦淮河清韵的人类。历史一页一页翻过,时光一年一年走过,世事变迁,世事缤纷,灵魂属于自己,本就是走马观花的我们又何必向秦淮河寻求些什么呢? 对秦淮河有了这样的理解,我的心蓦地清明起来。身临繁华却心如静水。而在这心的静水中,一支灵魂之桨在游弋,发出“汩汩的桨声”……
西塘流韵
走读嘉兴,最耐寻味的莫过于嘉兴地域上如星斗般闪烁的古镇了。比如西塘、乌镇、海宁等等。 西塘镇最让我钟情,因为这是一个生活了千年,而且至今还活着的古镇。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们赣南,古村镇如星罗棋布散落在乡村田野,但大多古镇毁于战乱或文革,即使少数保存得较好的古镇也都是躯体活着、魂灵死去了——其中不乏雕龙画凤的明清古宅,祠堂前也不乏如林的功名柱、高耸的旗杆石……但其中原始的生活状态随着如流的时光消解掉了,历史与文化的遗迹有了许多不经意的改变,卵石铺就的古驿道不见了踪影,宗祠雕花的础基成了垫坐石,世代相传的土语正在边缘化…… 而西塘则全然不同。这个江南著名的水乡,明清建筑基本完好地保留下来了,镇上人家的民风民俗及吴侬语言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了。直至今天,西塘成了全国著名的古镇,参观的人流络绎不绝,西塘也丝毫不改自己的做派,依然故我地生活在世代沿袭下来的生存环境与生活习惯中——临河的廊棚照旧是那么幽长那么曲折,划桨的乌蓬船照旧是那样飘泊那样荡漾;月亮照旧是把影子投到河水里投到院落里,太阳照旧是从桥东面升起桥西面落下;吴越的女儿家照旧是倚着窗棂儿梳妆打扮,人家的衣服照旧是挑在河面上迎风漫舞;闲适的人们照旧是打他们的麻将聊他们的闲天,纵横的巷弄照旧是深深浅浅宽宽窄窄;春天照旧是拂岸堤柳最撩人的季节,夏天照旧是“一口香棕子”最好卖的季节;秋天照旧是赏水灯看社戏最热闹的季节,冬天照旧是煮黄酒品香茗最温情的季节…… 乌镇西街甚至与西塘也有所不同。西街临近开放,但如同黎明前的夜晚,这里静悄悄的,除了少许施工收尾的工人,几乎没有人来往。诺大的古镇,只有我们这群参观者的身影与声音。区区百余人物,融入庞大的民居群,迅速便被小桥、流水、街巷吞没得无声无息。这便让人有一种美中不足的感觉。尽管这里也是河流纵横、小桥纵横,然而不见人家、没有旗幡,便只有风景,没有了韵味。可见,人,才是最重要的风景物。当然,若是我们晚半个月过去,当西街同东街一样住满了人家,活起来的时候,乌镇西街也必定韵味十足的。可我们毕竟早来了,看见的是还没复活的乌镇西街。 在西塘,尽管有一群一群来了又来的画人们常年守着人和景不知疲倦地画呀画呀,尽管有许多许多你来我往的游人们匆匆走过街和巷探头探脑地东张西望,五花八门的种种方言在这里交汇成缤纷的交响曲,陌生如斯的只只身影撞进西塘人的生活。然而,面对这一切外来的东西,西塘如入定的高僧,始终保持着依然故我的姿态,照样晨起暮歇、一日三餐,照样生自己的炉,喝自己的茶,画自己的画,走自己的路,读自己的书,丝毫也不做作、不骄躁,一点也不献媚、不露窘,仿佛一拔拔来去匆匆的行者只是紧一阵慢一阵的季风吹过而已。只是游人光顾得多了,西塘便做些行旅者的小生意。于是,在一面面展露风情的旗幡招引下,人们进入一个个深宅大院、花园庙堂,或流连于陈设精致的木雕馆、根艺馆、钮扣馆、瓦当陈列馆、黄酒陈列室,或陶醉于醉园的版画世界、倪宅的古色书香、西园的江南竹丝,或品啖于花雕、六月红、五香豆、八珍糕的芬芳……有的游人白天游累了,晚上干脆就住在了西塘,第二天接着游接着醉。如此,游人悠闲悠闲地逛了一巷又一弄,西塘是悠闲悠闲地过了一日又一天。这就是西塘,今天依然活着的西塘。 在西塘,很容易发现一个特征——这里的水很通情,总是把桥孔把旗幡非常清晰地倒映到其中,让摄影家的镜头躲也躲不开桥孔或旗幡的影子。桥是西塘历史的守望者,旗幡是西塘文化的传颂者,摄影家们则成了西塘的文明使者。西塘本来宁静如水沉默如桥,西塘一直这么寂寞、简单地生活着,忽然,千年来的这种寂寞、简单的生活成了让外面人敬仰的生活,成了摄影家眼中的模特与道具,于是,招摇风情的旗幡兴盛起来,如今宛如廊棚一般,廊有多长,幡就有多长。好在西塘就是西塘,骨子里并不为这些敬仰他们的人迷惑从而失去些什么,西塘依旧是小桥,流水,人家。
黑白苏州
最早对苏州的美好印象,是一句民间口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长大后,知道了落榜公子张继和他的《枫桥夜泊》。我惊叹他情怀惆怅,吟风弄月,捣鼓出的一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竟然醉倒往来客旅,诗化千年古城。好长时间,枫桥、寒山寺,乃至整个苏州城,在我心中衍化为愁绪疯长的故乡,或是幻想成诗情勃发的乐园。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先是读了余秋雨的《白发苏州》,苏州予我的印象成了一位白发飘飘的2500岁的长者形象;尔后又听过江珊的《江南水乡》,苏州予我的另一个印象则是水样温柔的秀江南!许多年以来,古老与风雅——便是我梦幻中的苏州。就是带着这种美好印象,今年盛夏的一天,我走进了古城苏州。 苏州是一个很容易寻找到感觉的城市。仅仅是走马观花式的粗粗阅读,就发现——苏州果然很老,枫桥、寒山寺、胥城、闾城……它们附丽的故事一个比一个老;苏州果然很雅,小桥、流水、人家、园林……其中散淡的韵致一处比一处风流。“忆昔吴王争霸日,歌钟满地上高台”,岁月深处,苏州是一片家园厚土;“姑苏夜雨放山茶,暗渡幽香醉万家”,折身之间,苏州是一抹秀色青青。 然而,最触动我心灵的,却并不是苏州的老或苏州的雅。这些都是早已为人稔熟的文化元素,是苏州文化的外化之物。我真正为苏州而心动的,是这座古城蔚为大观的黑白文化——成片成片的黑瓦白墙之民居,一匾一匾的黑底白字之店招。黑白苏州!——这就是我阅读中感知到的苏州形象,这就是我行走中体味到的苏州本色。我蓦然觉得,用“黑白”二字来描绘苏州,当真是太贴切了!我佩服这座城市——不管岁月如何流转,也不管世事如何变迁,尽情舒展城市花团锦簇式的繁华与小家碧玉式的华丽的同时,撷取城市历史与人文精粹,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取向,借助建筑和店招这一物的形式,以“黑白”之文化创意,构筑出了城市风姿绰约的形象外观。显然,黑白艺术充满智慧地显现了古城的精神特质,令苏州的灵魂在黑白分明的时空中轻舞飞扬起来。 没法考究,是哪个朝代开始起用了这种城市基础色,也不知道是哪位先贤创造了这种城市的精神表现形式?云岩寺塔静默,大运河无语,古城墙缄然。极有意义的是,两千多年的时间,苏州黑白风格的城市色彩丝毫没有被流水的时光冲刷、淡化,抑或变形。就在我往返与苏杭常几座城市之间的几天,我惊奇地发现,甚至一出苏州境域,相邻的浙杭就没有了这种黑白鲜明的城市色彩。显然,“黑白”只属于苏州! 其实,苏州给人最初印象本是柔美的——柔柔的吴侬软语、柔柔的苏州河水、柔柔的垂堤杨柳,美美的临河人家、美美的苏州园林、美美的丝绸苏绣,幽幽的曲巷、幽幽的流水、幽幽的茶肆,甜甜的小食、甜甜的评弹、甜甜的笑容……这个历史文化名城,2500年前一建城就是地位高贵的吴国都城。这个因伍子胥开掘护城河而筑就的古老城池,因为承载了太多的春花秋月,而流淌了太多的风流故事——自西施开始,苏州成了美女诞生的天堂,苏州城的女儿家们是一代代长成嫁人,苏州城的香樟是一棵棵地植了伐、伐了又植,小桥、流水旁的人家里吴侬软语是一直不停地呢喃至今;步陆机后尘,苏州还是文人辈出的故乡——张僧繇、陆探微、张旭、范仲淹、范成大、唐伯虎、文徵明、祝枝山、冯梦龙、金圣叹、叶圣陶,哪一个不是风流才子,哪一个不是用字或画或文在浇灌、养育苏州的柔美?每一个到过苏州的游人眼里,苏州就是那柔柔的《茉莉花》民歌,苏州就是那悠悠的寒山寺钟声。听过,思过,柔美、纯洁、神圣之苏州印象在我心中蓦然升华。 然而,苏州骨子里却是刚烈的。这种刚烈体现最鲜明处在苏州人身上。当然,最好的事例是开城祖伍子胥。伍子胥死后曾悬挂头颅于城门上,他死前交待,他要眼睁睁看着复仇的越国军队踏入吴国。传说,在越国军队走近胥城门口时,伍子胥那双未合上的双眼竟然喷出血光,令越军不得不绕往别的城门入城,后人赞曰:可怜国破忠臣死,日日东流生白波;还有一个人物也相当刚烈,他就是况钟。这位来自江西靖安的清官,明宣德年间出任苏州知府,刚正不阿,锐意改革,整顿吏治,削减高额田赋,减轻人民负担,兴修太湖水利,设置“济农仓”……苏州百姓亲切地唤他“况青天”;金圣叹,也是一位刚烈志士。史传,他颖敏绝世,奇才横溢,为人倜傥高奇,俯视一切,生性不羁,好饮酒,能文善诗,绝意仕进,善衡文评书,议论发前人所未发。明末清初,面对大明亡灭,普天之下,唯有金圣叹敢于发出呐喊,敢于放声痛哭,终以“大不敬罪”而被杀,是为著名的苏州“哭庙案”;明代,苏州织工大暴动更是威震朝野,“柔婉的苏州人这次是提着脑袋、踏着血泊冲击”京城的腐败统治,这次暴动的音响长久回荡在历史的天空,苏州第一次一改柔弱,有了血性而坚挺的姿态……无疑,这些人物和事件,为苏州树立起一座座历史丰碑,吴越大地耸立起一个个大写的“人”字。柔柔的苏州河水润物无声,浸染大地,也滋养着苏州人的刚烈情怀。听过,思过,凝重、粗犷、豪放的苏州形象在我心中蓦然崛起。 显然,苏州是既柔美又刚烈的,是黑白交融,是刚柔相济的。很多人对苏州黑白的理解很浅薄,认为黑白苏州仅仅是旧照片的视觉概念,仅仅是城市古老的一种简单诠释,全然不理会这座白发城市积淀深厚的文化内蕴,更不用心体验它于黑白色彩中坚守的文化骨格有多沉重。 不信,你往枫桥去,你会发现枫桥乃至苏州的所有拱桥,无不是棱角分明的石块在构筑圆拱;你往拙政园去,你会发现拙政园乃至苏州的所有园林中的点睛之物——太湖石,无不是形丑而质硬;你往绣房去,你会发现每一块锦绣图案,无不是钢针彩线在穿梭;你往剑池去,你会发现刚性的剑与柔情的水竟协和如斯——一池清水深藏宝剑三千…… 所以说,苏州这座城市给人的表象是柔美的,其内敛的精神特质却是刚烈的。只不过,黑白鲜明的民居建筑与店招,则将这一矛盾的人文表象与精神内质有机融合自然表现罢了。黑白苏州,是不是苏州真正的魂灵呢?
作者龚文瑞,笔名文瑞,中国作协会员,江西省作协理事,赣州市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赣州市散文学会会长,《散文视界》杂志主编,赣南日报副刊主编。多篇散文获国家、省新闻大奖,或入选《散文选刊》及各种年度散文选本,或被中学语文选作高考阅读题。 |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