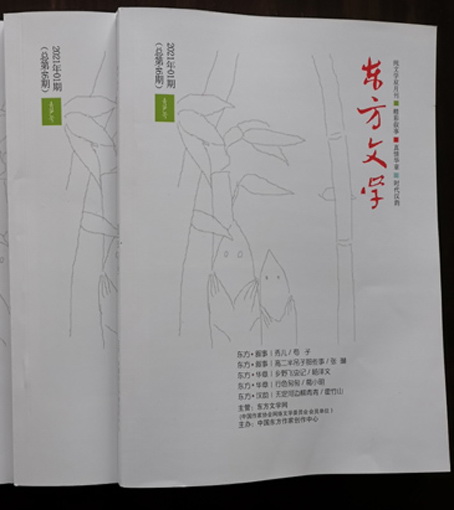亚托·帕西里纳也许在动笔之前就知道,用《当我们一起去跳海》作书名并在夏天发表,一定会被像我这样的“弱智”读者拿来当清凉消暑的书使劲翻。读了序言,我就捶脑袋,骂自己真笨:一群人约好一起去跳海显然不是要潜入海底“乘凉”……发觉自己“上当”,可“粘”在手上的书却“扯”不下来了。
“我们”一起去跳海不是消暑,那去做什么?找死!这本小说就是以找死队伍的结合、讨论、出发等为线索展开的,不止一次破产、身体状况不佳、孩子成年又成家远离、妻子对自己任何计划都不感兴趣的生意人欧尼·雷罗南决定自我了断。可当他带着枪来到一个废弃农舍,却发现连自杀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木桩上已站着一个军人正把系好的尼龙绳圈往自己脑袋上套……雷罗南大声制止后,一聊才知道,那个想死的军人名叫何马尼·坎裴南,原是芬兰东部某部队一名指挥官,因官场不得志才决定自杀的。谁知,这两个“臭味相投”的家伙越聊越投机,竟惺惺相惜、相见恨晚起来。最后,他俩创意把全芬兰有志于自杀的人集合起来,一方面劝服留恋生命的人重新面对人生,另一方面则组织一心想死者一起朝生命的终点迈进……让他俩“惊喜”的是,“征死”广告刊出8天后,竟有600多人积极响应,纷纷加入找死俱乐部。于是,这群认为生无可恋的家伙很快聚在一起,决心来一场有效率且震撼的“集体自杀”。经过讨论,这群找死的人最后选择集体乘游览车,一路冲进欧洲最北端的冰冷大海。然而,随着终点的接近,这群原本死意坚定的自杀者们,开始出现奇妙的变化:一些人又找到了不想死或不能死的理由……
看上去,“找死”是亚托·帕西里纳写作的唯一凭借,他笔下的那些厌世人物普遍感到,迎面而来的失语与困惑冷却了生活中的一切柔情蜜意,所以产生了“生不如死”的念头。其实他是以失落的生活信仰为题,对芬兰乃至当今现实社会进行不动声色的批判。位于欧洲北部的芬兰共和国,被誉为“千岛之国”或“千湖之国”,总人口530多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万欧元,是我国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几倍。应该说,芬兰是个环境很美、秩序很好、人很富裕的北欧国家,每年因凶杀等造成人命的恶性案件仅百起。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国每年因各种原因自杀的人数超过了5000、有自杀念头的更是高达5万多。为此,芬兰又成为世界上名副其实的自杀率高的国度。而生于1942年的亚托·帕西里纳,伐过木、制过衣、当过记者,所以他的关注点一直放在草根身上。他认为,芬兰人最大的敌人是犹豫、悲伤、麻木、脆弱等。可是,当他把笔触伸向那些厌世者时,往往又以正经中带着嘲弄、怜悯里掺杂讽刺的口吻,叙述着“想死者”的各种遭遇。所以,尽管他反映的是生命中沉痛的无奈,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从容的幽默与轻盈,并总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结局。就像《当我们一起去跳海》,一群找死的人经历从北欧到西欧各国特殊风光、体验不同风土人情后,他们的心灵却发生了脱胎换骨似的转变;又或许这群人觉得反正要死,什么都可以试,但就是因什么都能无所顾忌地去试,反而撞出了生命中更多的想不到可能。
有人说,《当我们一起去跳海》讲述的是生命乃至人生的哲学。不过,我却没见到“哲学”的影子,亚托·帕西里纳既没有宣扬“大家应该这样结束生命”的厌世意图,更没有大谈“蝼蚁尚且偷生”或“生命诚可贵”的生命哲学,而是透过吵吵闹闹的找死故事,揭示着人的生命中蕴藏着诸多变因和许多想不到的可能,这也许比空洞的说教式“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宣传更有说服力。尤其在当今时代,我们面对繁重的生活、生存压力,恐惧与焦虑与日俱增的时候,想到生命充满了许多未知,即便遇上最绝望的困境,也会鼓起生活的信心。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