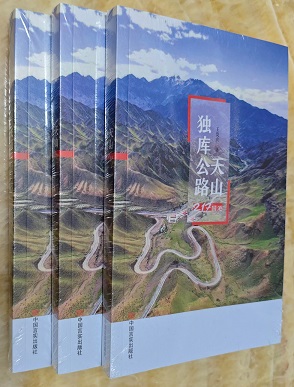孟繁华谈到,分析和评价世界文学视野中中国文学的创造性,是文学界当下一个热点议题,大家之所以集中地看到这个问题,他觉得折射出的是影响力弱势国家中作家、学者们某种寻求承认、认同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提出的是“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它更多地是强调学习借鉴,是跟随和融入;90年代以来,则是“在世界格局里的中国文学”,它已经悄然发生着转变,有了对差异性的重视。吴义勤说,不仅是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其实中国当代文学有着三条参照体系可供打量:世界文学的,古代文学的和现代文学的,世界文学只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在2000年之前,中国的现代性发生是滞后的,我们的确需要一个“先引进”“先学习”的步骤,这也是客观的。而在2000年之后,我们与世界性的同步已经建立,世界的发生与我们的发生已没有什么特别的时差,这时也就不再存在追赶的、学习的问题了。这种焦虑似乎已不再必要。而王春林则认为,强调在“世界文学视野中”,实际上是那种随着经济的强力发展而生出的大步前进的心态,它里面有躁气,是文化自信力、自尊心膨胀的结果。魏微感觉,这种强调不是自信而更多的是不自信,是试图证明,这也许会导致那些想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们把写作看成是策略性的,过于求大。她说,我愿意自己的写作是那种很微小的写作,把我在某一时间里所关心的问题用心地写出来。杨扬也谈到,“世界文学视野中”更多的是理论意义,对于创作而言它不太是问题。在这个时代,文学的中心已有转移,作家的出场、文学的写作更多变成个人的场域,个人化的、微小世界的写作应当给予尊重。
李云雷以欧洲对俄罗斯作家譬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接受为例谈到中国作品的国外评价问题,他说,近年来,中国作家对西方文学的了解甚至超过许多西方作家,我们的学习吸收做得已很充分,我们已经把西方文学传统带到了中国文学中来,并完成了自己的融合,至于能否及时被西方所接受,其过程是不可预知、设计的。——“可问题是,既然我们学习、吸收都足够充分,可一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为什么我们写下的多是那种千人一面、毫无文学魅力和创造性可言的所谓中国小说?”李浩说,把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视野中打量,不是姿态,不是所谓文化自尊或自卑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某种文学抱负,提出这样的问题完全是因为文学的自身,如果说它有焦虑,也是那种“影响的焦虑”,是在接受文学普世标准的前提下对差异和特别的强调。这样的议题,其实是想梳理和认知“我们的”和“世界的”之间的关系,是把世界文学当作我们的参照体系,借此审视我们文学的可能和问题,同时,也基于对当下下滑的、平庸的写作的不满。“我们的写作似乎太世故了,太庸常了,太成功学了,而不是试图致力为文学版图提供新的可能。”——孟繁华则强调,对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应看的是高端而不是低端,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平庸者占大多数,作家、批评家都不应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低端上,那种批评容易做出,但意义也不大。
至于要不要“世界文学”的参照体系,我们是否需要将对于世界文学的评判标准“拿来”,胡殷红特别提出,我们对于文学质量的评判标准急需理清,确立,现在它过于模糊过于功利了,这与批评家的下滑有相当的关系。而作家的评价标准是否会“正确”一些?那种强烈的个人偏好又会造成不够客观。我们不能把图书的发行量和受众多少来当作文学质量评判的标准,可时下,却时常如此。对此,李静认为,文学的评判标准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属于那种大家心知肚明但又无法做到量化的。处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关系问题其实更多的是处理价值评判的问题。她说,有些作家的作品,如果放置在世界文学的体系中来看可能意义不大,而假如我们在之外再建一个我们的标准的话,有些是挺有意义的,有些就可能被夸大。张学昕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借一位批评家的话谈到,相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中国有些作家也许算不上伟大。
孟繁华、吴义勤在发言中都谈到,中国文学如果在世界文学中确立位置,存在一个“价值观输出”的问题。吴义勤认为,在我们的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起同步关系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参与世界价值观的共造。东方化的文化价值观是世界多元中的一元,是差异性的存在,这里面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李静则从文学内部角度指出,文学当然有它的价值观,但如果我们把文学问题的争议放置在简单的价值观的层面,则有可能是对文学的某种伤害。文学,似乎更强调它的独特意味、魅力和自由的人性标准,以及那种个人的自我价值感。
发言中,许多作家、批评家还就文学和社会、生活、政治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王春林认为,我们的文学需要有效地介入政治,书写政治对人和世界的影响,因为它渗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角落中。而当下的中国文学则集体忽略、回避政治影响,这肯定会损害文学的力度。他说,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是有问题的,有偏差的,我们在理解和书写现实的时候把政治刨除在外,那它就是瘸腿的现实。艺术地处理文学和政治、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作家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李静也认为,政治是一个社会最有共享性的经验,它当然不能也不应遭到忽略,因为它部分地决定着一部作品的重量,尽管政治正确无法保证文学上的意义和不朽,它本质上还是艺术的。张学昕、王力平、孟繁华对此也都谈了自己的看法,张学昕说,对政治生活的有效书写可以将作品带到一个高度,目前,中国作家的问题是太聪明,对于许多作家来说技术已经不是问题。现在,是恢复对文学的敬畏感的问题,是抵御种种诱惑的问题,这点于当前更为重要。王力平说,在这个世界上,制作常有,而创造不常有,这是常态。对作家来说,更应“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魏微并不以为大和小、文学和社会及政治的关系值得如此强调,她说,作家更应当书写他所注意的、关心的,无论它在别人看来如何如何,这是无所谓的,这其实更是对内心的尊重。至于那些想进入文学史的作家,一直谋划着、策略性写作的作家,他们那样做也是他们的事儿。杨扬也认为,文学介入政治、为社会代言是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我们更应当看到,在现在,文学已有了多重的选择性,我们应注意这种变化,理解和认知这种变化。
研讨活动由李延青主持。相金科、关仁山代表河北省作协致词,他们强调,各位作家、批评家畅谈文学、深入交流,有益于把一些重要问题引向深入,有益于拓展河北文学的视野,促进河北文学及《长城》的发展。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