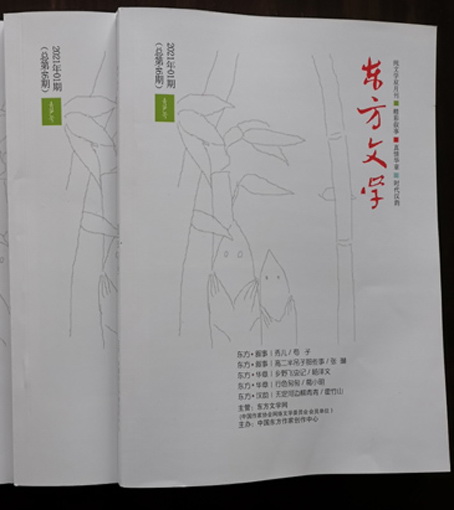1
在我看来,文学意识形态的激情缺失,就是一种文学的浪漫主义缺失。司汤达说,浪漫主义是现代的和有趣的,古典主义是老旧的和乏味的。歌德说浪漫主义是一种病,尼采反对歌德说浪漫主义是一种病的说法,他认为浪漫主义是一种良方,是用来治愈疾病的。瑞典批评家西斯蒙迪则说,浪漫主义是爱、宗教与骑士精神的结合。现在有人在提倡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我认为这是好事,这是一种社会性的民族文化救赎与启蒙行为。如何启蒙,如何救赎,则不是我们所能全部给出的答案。但是,一种迫切的历史召唤与民族文化愿景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之路,无法绕过自由浪漫主义的新启蒙进程。
以赛亚·伯林说,浪漫主义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浪漫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不仅是思想史,就连其他有关意识、观念、行为、道德、政治、美学方面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主导模式的历史。①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一书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阐述:
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是疾病、是堕落,是世纪病,是美丽的无情女子,是死亡之舞,其实就是死亡本身。是雪莱描绘的彩色玻璃的圆屋顶,也是它永恒的白色光芒,是生活斑斓的丰富,是生活的丰盈,是不可穷尽的多样性,是骚动、暴力、冲突、混沌;它又是安祥,是大写的“我是”的合一,是自然秩序的和谐一致,是天穹的音乐,是融入永恒的无所不包的精神。它是陌生的、异国情调的、奇异的、神秘的、超自然的;是废墟,是月光,是中魔的城堡,是狩猎的号角,是精灵,是巨人,是狮身鹫首的怪兽,是飞瀑,是弗洛斯河上古老的磨坊,是黑暗和黑暗的力量,是幽灵,是吸血鬼,是不可名状的恐惧,是非理性,是不可言说的东西。它又是令人感到亲切的,是对自己的独特传统一种熟悉的感觉,是对日常生活中愉快事物的欢悦,是习以为常的的视景,是知足的、单纯的、乡村民歌的声景——是面带玫瑰红晕的田野之子的健康快乐的智慧。它是远古的、历史的,是哥特大教堂,是暮霭中的古迹,是久远的家世,是不可分析的、人们愿意信守却无法表达出来的旧秩序,是摸不到、估不出的事物。它又是求新变异,是革命性的变化,是对短暂性的关注,是对活在当下的渴望,它拒绝知识,无视过去和将来,它是快乐而天真的乡村牧歌,是对瞬间的喜悦,是对永恒的意识。它是怀旧,是幻想,是迷醉的梦,是甜美的忧郁和苦涩的忧郁,是孤独,是放逐的苦痛,是被隔绝的感觉,是漫游于遥远的地方,特别是东方,漫游于遥远的年代,特别是中世纪。但它也是愉快的合作,一起投身于共同的创造之中,是对自己身在某个教会、某个阶级、某个党派、某个传统和某个伟大的、无所不包的、秩序井然的等级之中的意识,身在骑士、扈从、教会的等级之中、有机社会的关系之中或某个神秘组织之中的意识,正如巴雷斯所说,“大地与死者”,是身在共享一种信念、共居一片土地、共流一样血液、共有一样的祖先、同侪和后代的伟大社会之中的意识。它是司各特、骚塞、华兹华斯的保守主义,也是雪莱、毕希纳和司汤达的激进主义;是夏多布里昂美学意味的中世纪精神,也是米舍莱对中世纪的厌恶;它是卡莱尔的权威之崇拜,也是雨果对于权威的憎恨;它是极端的自然神秘主义,也是反自然主义的极端唯美主义;它是能量、力量、意志、青春,是自我的展现,它也是自虐、自残、自杀;它是原始的、单纯的、是自然的胸怀,是绿色的田野,是母牛的颈铃,是涓涓小溪,是无垠蓝天。然而,它也是花花公子,是打扮的欲望。红色的背心,绿色的假发,染成蓝色的假发,这就是内瓦尔在巴黎街头用线牵着溜达的龙虾。浪漫主义是爱出风头的,是怪癖,是为《欧那尼》一剧而战的战场,是倦怠,是生之厌倦,是萨丹纳帕路斯之死,不管是德拉克洛瓦的绘画,还是柏辽兹的音乐,还是拜伦的诗所描述的萨丹纳帕路斯之死。它是帝国、战争、屠杀、世界末日的震撼。它是浪漫主义的英雄——反叛者,厄运缠身的人,受诅咒的灵魂,是海盗、曼弗雷德们、异教徒们、拉腊们、该隐,是拜伦诗中的那些英雄。它是梅莫斯,是让·索伯格,所有的社会公敌,伊斯梅尔,所有处于十九世纪小说中心地位的纯洁的高等妓女和心志高尚的罪犯。它以人头为酒杯醉饮,它是攀登维苏埃火山与同类灵魂对话的柏辽兹,它是撒旦的狂欢,是愤世嫉俗的讽刺,是魔鬼般的笑声,是黑色的英雄。它也是布莱克想象中的上帝和他的天使,是伟大的基督教会,永恒的秩序和“不足发表达基督灵魂的无限与永恒的布满繁星的天空”。简言之,浪漫主义是统一性与多样性。它是对独特细节的逼真再现,比如那些逼真的自然绘画;也是神秘模糊、令人悸动的勾勒。它是美,也是丑;它是为艺术而艺术,也是拯救社会的工具;它是有力的,也是软弱的;它是个人的,也是集体的;它是纯洁也是堕落,是革命也是反动,是和平也是战争,是对生命的爱也是对死亡的爱。②
我们需要重新返回中国传统诗学的领地吗?事实上,我们已经回不去了,我们这一群现代人已无法回到古代的典籍丛林。在回不去的历史现实面前,一部分既留恋传统诗学又追求自由独立精神的诗人于是选择了新古典主义,来弥补传统诗学中自由主义的缺失,寻求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多元向度。有人把追求新古典主义诗学的诗人称之为“复古派诗人”,甚至带有浓郁的孤立与嘲讽意味,我认为这种诗学层面的粗略评判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公正的。新古典主义也并非什么腐朽的不可行的美学概念,18世纪的新古典主义创立者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就提倡“古迹的主观化”,他以原旨的浪漫主义激情来响应古希腊艺术,正因如此,他预言了浪漫主义美学必将盛行于后世的西方与东方。而在中国当代诗学领域流行的新古典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浪漫化的古典主义。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的歌德在理解古典主义时,仍然没有否定古典主义的历史性意义,他说古典主义也是强健的、鲜活的、愉快的、合理的,如荷马史诗和尼伯龙根之歌,正是因为这种观念使然,促使他晚年完成了诗歌巨著《浮士德》。回顾西方的近现代诗歌史,我们不难发现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大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浪漫主义时期。这些国家先后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这些西欧国家的诗歌历史往往是与它们所经历的文化启蒙——浪漫主义启蒙运动紧密相联的,换句话说,西方诗歌与西方哲学一样占据着西方文化史的同等重要的主导地位。当我们回顾中国的新诗史,就会发现,正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影响了中国一代学学人与诗人。清末至五四时期中国涌现了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吴虞、胡适、吴稚晖、林语堂、殷海光、傅斯年、雷震、梁实秋等,其中浪漫主义诗人主要以苏曼殊、徐志摩、查良铮、早期的郭沫若等为代表。然而,这种西方浪漫主义文化无论是对中国思想领域的渗透,还是对文化领域的渲染,都是短暂的,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文化思潮,这种现象无疑是具有历史局限性的。
这里,我所要强调的诗歌精神并非就是一种纯粹的传统浪漫主义,停留在中西方十八世纪或二十世纪的抒情浪漫主义。我心中所想象的诗歌理想,必须具有“意识形态激情”,这种激情不仅仅是浪漫的,抒情的,更应该是自由的,忧患的,幽暗的。因此,我更愿意把“后天诗群”追寻的这种自由诗歌理想称之为“自由浪漫主义”——一种启蒙式的现代诗歌理想。福柯说,“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③事实上,我们身处的中国社会正处于一种文化的现代性的启蒙状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哈贝马斯说,只有继续启蒙才能克服启蒙带来的弊病。然而,新世纪十年过去了,我仍然一片茫然,中国诗人在一些重大事件面前大面积地失语,失声,逐步渐模糊和丧失了诗性正义的立场。在今天,我不禁要问,我们的自由诗歌理想在哪里?
2
20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编年史家哈罗德·斯特恩斯(1891-1943)发现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逃往欧洲,他于是在1921年的著作《美国和青年知识分子》中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的知识分子在哪里?”,随后,他也像众多美国知识分子一样,成为 “失落的一代” 中的一员。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回首往事,“1989-2009”,我们的知识分子同样在这20年中成为“失落的一代”。如今,20年过去了,当年热血沸腾的充满社会正义与人文理想的知识分子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
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同样,当我们回首百年往事,清醒地发现,当今之中国现状与上世纪的五四时期极为相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由浪漫主义中国化与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国粹主义)东方化,是五四运动以来主导中国社会发展三大思潮,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泛和平崛起”(这是我本人首次在本文中提出的概念。尽管在我看来,这种泛和平崛起,也许是一种当下中国特色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假象混合集成反应,以及中国政治文化策略层面的蒙蔽效应),中国未来的道路发展的方向,促使着中国新一代主流、非主流的知识分子正急切地进行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大思考与大博弈,并且涌动出他们同台竞技或同室操戈的多元文化思潮的文化重构的激烈景象。本雅明在《打开的我的书》中说到:“所有的激情都建立在混乱的基础上;收集事物者的激情建立在混乱的记忆上,”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呈现的“意识形态激情”现状,的确如此。
当代中国诗人的意识形态的激情缺失与群体性精神逃亡现象,一直没有引起文化批评界的足够重视,更没有引起诗人们身身的觉醒与反思;相反,中国诗人回归传统诗学的自恋情节却在不断上升。这种现象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全球现代性诗学的角度重新反思中国传统诗学的自恋问题。1966年至上世纪末,中国又出现了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诗人,其中以食指、黄翔、北岛、昌耀、廖亦武、贝岭、京不特、黄梁、黄灿然、李笠、姚风等重要诗人。21世纪初,新一代具有独立意识的诗人在70后诗群中产生,比如朵渔、孙磊、廖伟棠、沈浩波、蒋浩、黄礼孩、杨典、杜撰、徐淳刚、吴季、方闲海、赵卡、曾蒙、张杰、李建春、余丛、育邦、贾冬阳、江非、霍俊明、广子、胡应鹏、花枪、阿尔、巫昂、吕约等,这一群不可忽视的70后诗人,正在成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诗歌的中坚力量,同样这种诗歌理想与自由精神,在60后与80后诗人中也得到了体现,只是他们的诗学理想与反抗精神没有这一群70后诗人如此突出,来得如此迅猛。为什么70后诗人中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敢于担当,敢于批判现实社会的独立诗人呢?这无疑这一批诗人成长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有较大关系,与70后诗人所面临的时代困境与诗歌困境有重要关系,正是这种复杂的时代背景与诗学背景,让这一批70后诗人开始觉醒,自觉地在汉诗现代性言词中背负与消解时代的诟病与顽疾。作为个体的诗歌写作者,我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与感召。
如今,当我们反观中国当下的日常社会文化与消费文化时,我们已经深深地发现,流氓文化、痞子文化、媚俗文化已经充斥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角落,一个精神病人或者一个变态狂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大众娱乐的明星,比如眼神充满恐惧的犀利哥被改造成了“中国时尚先生”,相貌奇特的凤姐一夜之间变成了前后五百年无人能敌的“文化先痴”;电视娱乐走秀的马诺、闫月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中国当下性文化的“肉色符号”……,正如批评家朱大可所言,我们这个时代正在上演着一场宏大的流氓盛宴。如果说,这种流氓盛宴是一种集体性的“肉体亢奋”,那么中国当下社会文化呈现出的对社会道德、文化伦理、人文思想、独立精神的漠视,则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疲软”。作为时代境遇中的诗人,我们无法逃避这种时代消费文化的现代性的诟病,我们必须通过诗人心声与言词,来消解与对抗这种堕落的丧失社会进步意识的低俗文化,这种消解与对抗是否有效,我们应该将它视为诗人的一种诗歌理想,同样我愿意把这种写作上的努力姿态,视为“自由诗学理想”的一部分,现代性“诗学正义”的一部分。
3
我们必须重提中国当下诗歌的“现代性”。上个世纪,本雅明在其诗性哲学研究中隐喻性地发现了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拾垃圾者”形象,这是一个重大的文化事件,一个不朽的预言。我认为,本雅明的“拾垃圾者”形象,较生动地体现了诗人的“现代性”身份。诗歌的“现代性”既包含着浪漫主义的情怀,同时又有自由主义的表达。波德莱尔也曾在“1846年的沙龙”一书中说过,说谈论浪漫主义就是谈论现代艺术。因此,我更愿意把当下诗歌的“现代性”归结为一种具有自由浪漫主义思想的诗学特征。美国学者劳伦斯·E·卡洪说,“现代性的当代困境中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现代文化中某种令人难以捉摸、但却十分重要的气质在逐步地自我削弱,”他认为全球文化的现代性正陷入困境,“进退维谷,逐渐枯萎丧失了自信力,丧失了对于将来的意识,丧失了对于它自己的合法性的判别力”,他还认为当下的知识分子们不应该容忍“现代性悄无声息地死去,因为它所取得的功绩会与之偕忘 ,其中就有人道主义与民主”。因此,现代性需要注入新的活力,诗歌的现代性同样是如此。④
一百年即将过去,一代代的诗人与思想者,一直在追寻着他们时代的“拾垃圾者”。谁是我们今天的“拾垃圾者”?在我们这个时代,一直不乏一批杰出的“拾垃圾者”,比如林昭、北岛、王小波、艾未未、金锋、崔卫平、徐贲、朱大可、崔健、胡杰、廖亦武、冉云飞、张元、贾樟柯、周云蓬、左小诅咒等;从某种意义上出发,我愿意把“后来者”形象,视为“拾垃圾者”形象的另一个外延式的阐释。同样,在我们这一群诗人中间,正潜行着一群“后来者”—— 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诗人,他们视“拾垃圾者”为自己精神道路上的路标,理想人生的引路人。他们正在路上,他们正在成长着。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何时会产生像策兰、米沃什、布罗茨基、帕斯捷尔纳克、曼杰什坦姆、巴列霍、金斯堡、阿多尼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这样的充满“意识形态激情”的杰出诗人?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在我看来,中国当下一大批知识分子正逐步丧失时代之记忆与个体之尊严,其中诗人也不例外。青年学者贺奕在《群体性精神逃亡: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纪病》中一文提及“群体性”概念正是历史为中国知识分子设下的迷障——“正是这种个人向着群体,群体向着群体的群体无休止的精神逃亡过程,折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人格上的先天缺陷。”
在我看来,中国当下诗歌现代性的活力,正是来源于中国的当代文化的新启蒙运动,来源于这一群杰出的“拾垃圾者”的影响力。他们都葆有一颗诗人的心灵。诗人的心灵,永远是孤独的心灵,危险的心灵。当诗人堕入安逸与保守的时代境遇之中,那么诗人的社会性精神价值,荡然无存,甚至会成为太儒主义者的摆设品与附庸物。当一个时代突然出现一个被诅咒的诗人,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时代是有福的。波德莱尔对于19世纪的法兰西来说,不正是一个被诅咒的诗人吗?他的忧郁,感染着巴黎的忧郁;他的愤怒,激动着巴黎的愤怒。或许,21世纪的今日中国,正在诞生波德莱尔式的充满寓言意味的诗人,唯有这样的诗人才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为杰出的心灵。海德格尔说,“诗人是在世界的黑夜更深地潜入存在的命运的人,是一个更大的冒险者;他用自己的冒险探入存在的深渊,并用歌声把它敞露在灵魂世界的言谈之中。”⑤
一百五十年过去了,波德莱尔笔下的现代性“恶之花”,再一次在中国的大地上开放,悲剧性的寓言式的开放。如今,中国当下具有独立意识的诗人笔下,开始涌动着中国的忧郁与愤怒,以及时代之恶,社会之恶,人性之恶。尽管柏拉图试图将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国,但是人类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诗人被永久地放逐于人类的心脏,成为人类灵魂最忠诚的救赎者。事实上,诗歌正是人类自由理想与人类道德的最理想的化身,诗人正是这种精神力量的持有者,这种力量是哲学家所不可具备的。也许正是基于这种恐惧,柏拉图对诗人持有一种隐秘的偏见。诗意的力量是无穷大的,比如诗人的悲剧性、诗歌的伦理与道德、诗歌的现代性、诗歌的自由主义理想等,均有着政治、哲学、经济、艺术等领域所不可替代的文学作用。正是因为这一点,无数的哲学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和政治家都在漫长的一生中热爱着诗歌。正是诗人,在黑暗中,通过诗意的力量、诗性的感悟给我们带来光亮。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无信仰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人文的现代性开始走向没落,走向黑暗,诗歌的现代性同样误入歧途。现实中诗歌的写作和阅读,已陷入一阵彼此漠视、彼此尴尬、彼此争斗的多难境地,这个时代早已不需要自由正义的诗歌理想,真正的诗歌理想困顿在诗人的心中,而不是掌握在意识形态中。正是基于对当下诗歌写作精神的探求与努力,“后天”诗群更愿意成为一群安静的写作者,一群“后来者”,坚持学习与操守,坚持一种不在场的“后来写作”。
4
“后来写作”理念,最早在2005年由我提出。“后来写作”主要强调一种什么样的写作姿态与写作观念呢?简而言之,“后来写作”最重要的写作特征那就是强调坚持诗歌的现代性与诗性正义,坚持诗人的自由意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
从全球视野的现代诗学角度,我们既要继承兰波、波德莱尔、金斯堡、叶芝的现代性,又要继承策兰、里尔克、米沃什、布罗茨基等杰出诗人的现代性;我们既要继承以北岛、顾城、多多、杨炼为代表的今天派诗人的现代性,又要继承以于坚、韩东、柏桦、翟永明、张枣、吕德安、西川、杨键、雷平阳、余怒、伊沙、余笑忠、哑石、沈方、黄斌等以多元诗学特征为代表的中国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性。当然,现代性的确也是多元的,我们应该本着批判与吸收的态度来审视他们的诗歌,从中寻找自己想要追随的时代精神与诗歌理想的参照物。正如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列举现代性五副面孔,我赞成他的一种观点,他认为,现代性与历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而且预示着一种精神冒险行为。⑥这种对立的现代性诗学曾经体现在波德莱尔的现代性诗歌美学之中,如今中国当下的诗歌现代性同样遭遇了历史性的悲喜剧:毛主义、无信仰的国家叙事、八九事件、乌托邦、极权主义、流氓文化、新启蒙运动、新儒家文化、市场经济、后改革运动、GDP运动、灾难中国……。由于种种多元对立的现代性的相互纠合,导致中国当下的社会现状与文化现象,开始显露出西方正盛行的“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反现代性”、“不确定性”与“不可决定性”。哈贝马斯在他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把尼采作为转折性的开启后现代性的标志人物,在德里达看来,这是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观点。哈贝马斯认为《悲剧的产生》一书具有进时代的意义,应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其意义就在于尼采转向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精神。哈贝马斯认为,尼采明确地要用审美来替代哲学,世界只能被证明为审美对象。⑦哈贝马斯的话的确让我感到,后现代性似乎增加了现代性中所匮乏的形而上诗学理想。形而上诗学理想,其实仍然是每一个现代性诗人所渴望坚守的东西:过去与未来的对抗,现实与诗意的对抗,文学与哲学的对抗。
当“先锋性”这个概念从早期的战争语言中脱胎而出,进入到文学艺术的境地之后,逐步被诗人与艺术家们加以通俗化。当人们大肆谈论先锋性的时候,我更愿意把先锋性视为现代性的一个特例来认识,或者说,诗歌的先锋性让我们看到了诗歌审美的极致与积极性。甚至我们应该看到,诗歌的先锋性更容易被它的读者所接受,所认知。所以说,先锋性的命运,同现代性的命运,如出一辙,总是处于一种进行时,更容易让我们窥视到时代性的文化艺术的真相与写作者的诉求。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非常强调诗性正义的诗人,诗性正义几乎贯穿了他全部的诗歌和他的一生。他用一种诗化的言词来称颂诗人的“裁判”身份:“他是各种事物的仲裁人,他是司铎,/他是他的时代和国家的平衡器,……/他以自己的坚定信念力挽狂澜,避免时代背信的趋势,/他不是辩士,他是裁判(大自然绝对承认他)/他不像法官那样裁判,而是像阳光倾注到一个无助者的周围,……/他看出永恒就在男人和女人身上,他不把男人和女人看虚幻或卑微。”⑧我从策兰、米沃什、布罗茨基、巴列霍、阿多尼斯等诗人身上,同样看到了伟大的现代性的诗性正义,同样,我们也可以从屈原、杜甫、李白、苏东坡、钱谦益、龚自珍、陈寅恪等诗人的身上,看到古典性的诗性正义。而我们这个时代,有多少诗人一直在坚守着诗性正义呢?我们正期待着,我期待诗性正义正流淌在我们中间。
谈及诗人的自由意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时,事实上已经关切到诗人的命运,“后来者”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在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自由意识、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相对而言是并不匮乏的,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醒目的写作群体。因此,我这里想着重谈谈这三种意识,对于一个胸怀天下的诗人的写作与思考所构成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过,“我们都宣称主张自由,但在使用同一个语词的时候,我们并不总是指称同一个事物。”我这里强调诗人的自由意识,仅仅是指诗人应该在时代的大潮中,敢于担当,敢于言说,像乌鸦一样地歌唱,引领黑暗时代的人们的饥渴,做“他时代”的启蒙者与先驱。那么,诗人的忧患意识又是指什么呢?这一点我想是比较好理解的。中国古代诗人中,很多都是诗歌忧患意识的杰出典范,比如诗人屈原:“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李白:“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穷年忧黎元,叹息胀内热”;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等等,这些诗句生动深刻地表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与悲悯情怀。近代诗人龚自珍有首诗的题目就叫《赋忧患》:故物人寰少,犹蒙忧患俱。春深恒作伴,宵梦亦先驱。不逐年华改,难同逝水徂。多情谁似汝?未忍托禳巫。”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六》中他又说:“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这里不仅明确指出了“忧患”,而且是“大忧”“大患”。真正的大诗人的心中就应该有这种“大忧”与“大患”。
“幽暗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著名学者张灏先生于1980年提出,他说:“所谓幽暗意识是发自对人性中与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因为这些黑暗势力根深蒂固,这个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圆满,而人的生命才有种种的丑恶,种种的遗憾。”⑨在张灏先生看来,西方文化中的幽暗意识,经由入世精神的发展,对政治社会,尤其是自由主义的演进,曾有极重要的进步影响;他同时认为,东方文化中的儒家传统,同样存在着幽暗意识,并且与成德意识相为表里。说到这里,“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有什么区别呢?张灏先生有这样一段精彩论述:
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有相当的契合,因为幽暗意识对人世也有同样的警觉。至于对忧患的根源的解释,忧患意识与幽暗意识则有契合也有重要的分歧。二者都有相信人世的忧患与人内在的阴暗面是分不开的。但儒家相信人性的阴暗,透过个人的精神修养可以根除,而幽暗意识则认为人性中的阴暗面是无法根除,永远潜伏的。不记得谁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上人类的文明有进步,但人性却没有进步。”这个洞见就是幽暗意识的一个极好的注脚。⑩
最近,著名学者崔卫平做了一个演讲,题目就叫《这个时代的忧患和幽暗》,我个人认为正切中我们当下诗歌疲软的要害,我恳请大家找来看看,也许对我们这个黑窑时代的诗歌写作带来警示。
总而言之,“后来写作”是一种新启蒙文化倾向的诗歌写作,是一种具有现代性与先锋性的未来写作范式,是一种具有双重历险的独立写作范式。这种独立写作的难度被我视为一种“双重历险”,主要体现在语言诗学层面的历险与诗歌精神层面的历险,解决了这种“双重历险”,诗歌写作将会使我们的诗歌写作进入一个新的诗学高度,历史性的高度。
5
“我们”。像杰克·凯鲁亚克一样,尚未找到灵魂的家园,所以集体地在路上。“我们”,依然是在路上的人,在暗夜中,在生活的峡谷,用诗歌的方式去努力触摸时代的私处,触摸到的感觉,和“他们”是大不一致的。“我们”,没有今天和明天,我们只有后天,我深信只有在“后天”才会产生“后来者”。
时间过得太快,我们的身心已无法回到上个世纪。当我们在写作生涯中使用“回忆”、“纪念”、“缅怀”、“革命”、“先锋”等字眼时,已是一种文化精神的假象,一种不在场的历史复叙事。这个时代,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是过去,还是未来,谁也说不清。诗人的心里都有着一本帐,语言帐,灵魂帐,真理帐,可诗人们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会算帐的人。一个成熟大气的诗人像是手艺精湛的会计师,谁在腐败,谁在盗窃,谁在堕落,谁在合谋,他心里最清楚。他又像是那个眺望灯塔的守夜人,时刻警醒着,在黑暗时代的浪尖……
① 参见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享利哈代编,吕梁等译, 2008年,译林版,第10页。
② 同上,第23-25页。
③ 参见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福柯:《什么是启蒙?》,三联版,433-434页。
④ 参见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与反文化》,王志宏译,2008年,商务印书馆,第7-9页。
⑤ 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1989年,三联版,第9页。
⑥ 参见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 2002年,商务印书馆,第59-61页。
⑦ 参见陈晓明:《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200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5-6页。
⑧ 参见玛莎·努斯鲍姆:《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丁晓东译,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18页。
⑨ 参见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2006年,新星出版社,第24页。
⑩ 同上,第309页。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