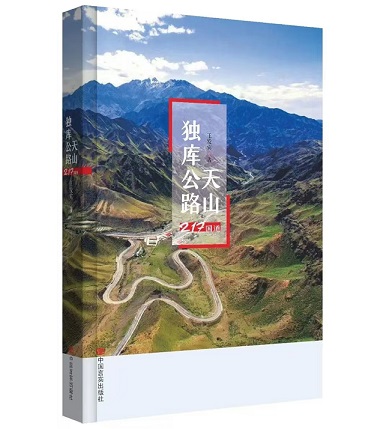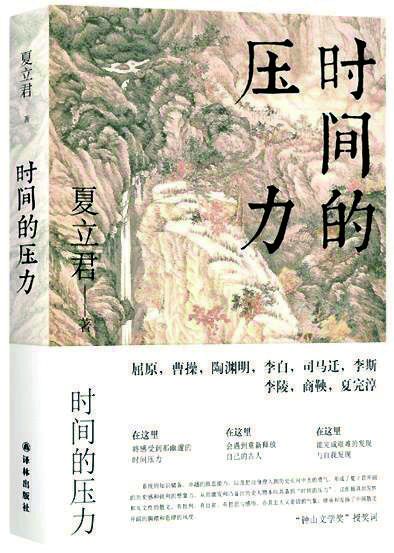
我与夏立君认识是因为一棵树。
我爱树,尤其钟爱那些跨越漫长岁月、负载着深厚人文信息的古树。山东日照市莒县有一棵3000多岁老银杏,我前后四次去拜望。此树令我联想到中华图腾“华表”,我称之为“有生命的华表”。我为这棵树写了篇长文。夏立君给我提供了许多资料,我于是知道他是一个踏实的人。
多年前首次拜望这棵树时,就有当地作者夏立君作陪。他那有些单薄的形象,在大树下似愈显安静内敛。我很快发现,这亦是个喜欢树的作家。他的首部文集《心中的风景》中有数篇写树的文章。“到大树下站一站,我相信,你的心情会好起来。”(《大树》)“世上的根都是诚恳、沉默、坚忍的。生命的力量就是根的力量。每棵草、每棵树都有根,人难道可以无吗?”(《根》)这都是夏立君二三十岁做中学教师时写的文章。青春朝气,一望而知。
始于大树下的忘年交一直持续着。我常让他给我在当地寻觅资料,亦经常在邮件或电话里谈老银杏或其他话题。当7年前,我读他的又一部书稿《时间之箭》时,颇感震惊:青春小树已成气象可观之树了。当时我就说:“像《时间之箭》《在西域读李白》这种水准的文章,若能有10篇、20篇,想一想,立君是何等分量?”这是鼓励,亦是期待。
又是多年基本默默无闻。似乎是忽然之间,《时间的压力》出版了!这回,分量可真是出来了。“气象可观之树”,成为望之蔚然、即之成荫的大树了。细读一下,那股非同一般的阅读快感再次弥漫而来。面对白纸黑字,“水落石出”这一阅读感受更强烈了。夏立君涌起泱泱之水,然后“水落石出”。是的,水落石出,吹沙见金,扼腕长叹,就是这个味道。
言说传统、言说古人,可浅可深。浅易,深难;戏说易,实说难。夏立君说:他把理解杰出古人当作对传统的一种回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伟构想里,中华传统何为?这无疑是时代大课题。作为我们生存背景的传统,营养与糟粕俱在。怕就怕将古董皆视为“艳若桃花,美如乳酪”。在个人独见与时代精神结合中,夏立君强烈表达了他对传统的温情回归与深刻反省,是理性与情感的深度交织。他的发现与卓识,他的执著或偏见,都是清楚的。
这是独辟蹊径之文,自立格局之文,言他人所未言之文。夏立君彻底拉开了与煽情文、鸡汤文、掉书袋文的距离。“学术质地的文学表达”、“学者型作家”,对他的这类判断,我赞成。立君每写一人,总是深挖古今资料,旁及中外文史哲,一文耗时半年、一年甚至更久。文章里的每句话都可印证——他的根扎得多深啊。这等功夫,谁人能下?“大树气象”绝不可能靠捷径靠取巧而生成。对此,我心戚戚。范仲淹说:“噫!微斯人,吾谁与归?”肯这样吃苦的人实在太少了。
对立君,我一直以小夏呼之。小夏不小了,已50多岁了。他只在近数年始能将主要时间投入写作。自《时间之箭》之后,7年仅成此一书。从《时间之箭》到《时间的压力》,这步幅可真够大。《时间之箭》里有部分品质过硬文章,《时间的压力》则是一个“系统”过硬了。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已经是开拓新视野、贡献新东西的境界了。我相信,这是本不会在泱泱之水里打个漂就不见了的书,是能在时间里停留的书。一位基层作者,实现了似乎难以实现的目标。作为文学兼新闻的同道,夏立君不负我望。有人已用“大器晚成”来评价他。在我眼里,立君固然已具大器之质,但离年龄意义上的“晚”尚远呢。一位作家,若在50岁开外对文学及人生大情大理开窍,何尝晚哉!怕就怕一窍未开呢,却自以为“洞”比天大。
在美丽海滨城市日照,有一棵“华表之木老银杏”,有一位默默苦斗的作家夏立君。这两者当然不能等量齐观,但“根深叶茂”却是事物成长的铁律。用根底深浅去观察掂量一位作家,是可靠的管用的。对老银杏,我瞻仰又思考;对夏立君,我愿意继续期待之。
我喜欢大树,喜欢并追求有大树气象的文章。(梁衡)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