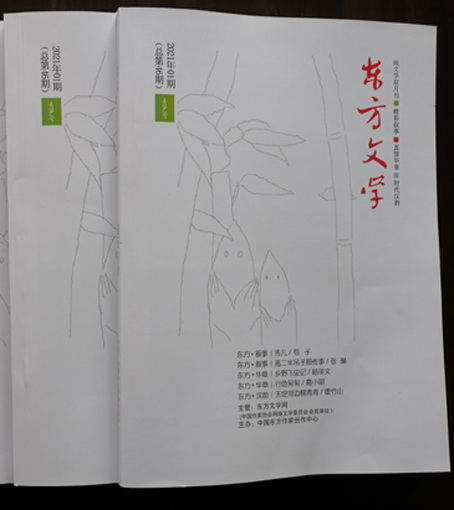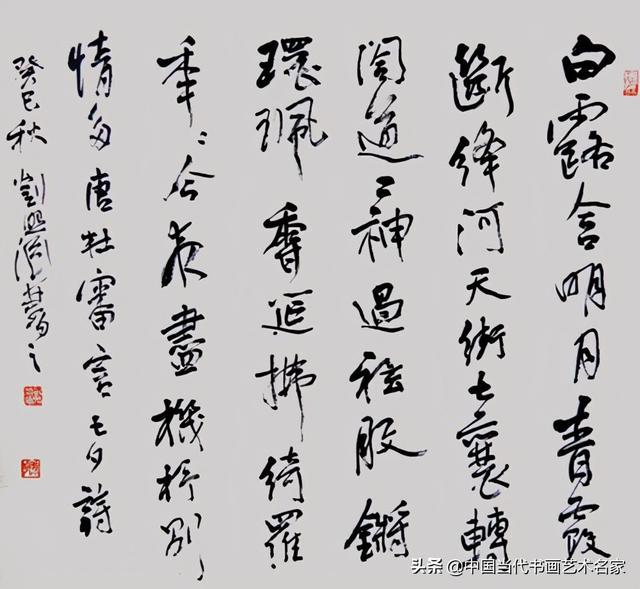时间长了,习惯了,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鲁院的主人。给朋友打电话,不自觉地就说出了“我们鲁院”这样的话,引来朋友的调侃。猛然一惊,这话怎么就顺溜出来了呢?其实吧,这人啊,在换到某一个新环境的时候,开始可能不习惯,待的时间一长,也许真就找不着北,就把自己也融入新环境中去了。
在京城这样一个人多车多、噪音不断的地方,鲁院却是少有的清静。走在草坪间的小路上,穿行在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不去仰望周边的高楼大厦,真就以为这是一块静土田园,是给人以修身养性的福地。乌鸦在高空盘旋,喜鹊在树尖鸣叫,还有几只懒猫出没在树丛间,这样的环境再加以内心的想象,就会氤氲出一股慵懒的心境。假如阳光再温暖一些,我肯定会躺到草坪上去,就像躺在乡间田埂上那样,随手抓一把青草放在鼻子边,用一股深呼吸来品尝青草的馨香。
除了草坪,鲁院门前的池塘是我光顾得最多的地方。刚进校时,看到池塘里结着厚厚的冰块,以为塘里不会有活着的生命存在。到校的第二天早上,我想看看池塘里的冰块到底有多厚,就找来一根木棍,趁早上没人时走到池塘边,用木棍去捣冰块,结果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把冰块捣碎。由此才知道,北方的冰是真正的冰,当这些冰在水上形成的时候,已经和水紧紧拧在了一起,而不是像南方的冰那样,只是在水面上铺出薄薄的一层,走在边上声音放大一点,似乎那一层薄冰就会被震碎。
突然有一天,当太阳出来的时候,冰层下出现了一群红色的鲤鱼。这些鲤鱼贴着冰层缓慢游动着,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让自己的身体慵懒地静止在冰层下面,慢慢享受着透过冰层的阳光沐浴。那一刻,我感到很震惊。我的震惊是有理由的,这缘于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厚的冰块,更没有想到在这么厚的冰块下,还潜藏着如此美丽、如此富有活力的生命。
阳光一天天温暖起来,池塘里的冰也一天天化去,出现在水面上的鱼群也越来越多。没想到这么小的池塘居然生活着这么一大群鱼,当它们全部浮出水面,池塘的每一个角落就挤满了它们的身影。冰融化了,浮出水面的鱼儿就成了猫们的诱饵,每天清早,在太阳出来之前,都有那么几只猫,在池塘边上走来走去地巡视着,或者就一动不动地蹲在池塘边上,虎视眈眈地盯着水面,盯着那些游动的鱼群。神奇的是一天早上我刚走到池塘边,正好看见一只猫抓住了一条鱼,还没等我仔细看清楚,猫就叼着鱼跑向了远处。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猫捕鱼,而且是在鲁院这个散发着浓浓文化气息的地方,猫捕鱼也就多了一点文化的元素。鱼的悠闲,猫的蹲守,以及鱼对阳光的渴望,猫对鱼的渴望,都自然而然地组合成了一幅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活画卷。能够从水中把鱼捞上来,这样的猫应该很不简单,而且这些猫关注池塘、关注池塘里的鱼,也应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春在鲁院蠢蠢欲动。最早的声音是那些发情的猫叫出来的,它们躲在树丛或者竹林里,而把那种凄婉的叫声充斥在房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鲁院的猫真多,常常不经意间,就会看到猫的身影在眼前晃动。据说八里庄的那个老鲁院,流浪的猫更多,难道猫们也喜欢聚会在有文化品位的地方?猫们的叫声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北风渐渐减弱,一些迫不及待的小树慢慢舒展身子,开始做迎春的准备。
北方的春来得很缓慢,应该是踩着循序渐进的步伐走来。不像我所生活的南方,春总是来得很猛烈,头一天晚上,树上除了光秃秃的枝干还什么都看不到,第二天早上起床,猛然间就看到很多枝干上已经冒出了新芽。而这里的一些树,芽苞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就是还看不到枝叶冒出来。也许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漫长的等待,才让我每天出门的时候,总是留意这些苞芽,渴望看到它们长出绿叶的样子。
一些母猫的肚子大了,猫们凄婉的叫声也慢慢停歇了,一场雨过后,缓慢走来的春意更浓了。乌鸦和喜鹊是在鲁院的树丛中见到最多的两种鸟,乌鸦常常盘旋在高空,而喜鹊却常常站在树上。它们沿着各自不同的生活轨迹,在天空或者在树与树之间,呼朋唤友,飞来荡去。不知道京城这片土地,怎么会有那么多乌鸦,在我生活的那片土地上,乌鸦已经绝迹30多年了。
日子不紧不慢地过着,这种有规律的生活反而让人很懒惰,听课、看书,看书、听课,周而复始的作息方式让人总是犯困,仿佛睡不够。经常到院门前的草坪中走走,听听在树枝间搅动的风声,闻闻那些含苞小树的气息。然后每天都会来到池塘边,看那些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下午又注意到一只猫守在池塘边,我走过去的时候,猫盯着我看,直到我快走到它身边,它才不情愿地起身离开。猫不愿意看到我,更不愿意我去打扰它的生活。我不喜欢乌鸦,而却无法躲避乌鸦的叫声。就在我走近池塘的时候,一群乌鸦从头顶上飞过,一阵乌鸦的叫声回响在耳边……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