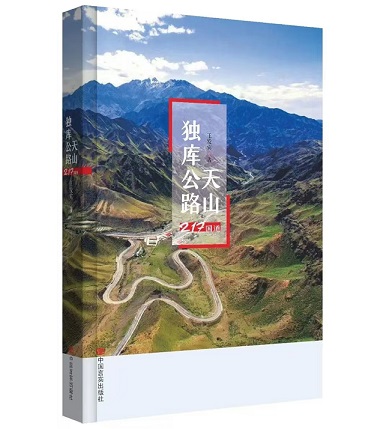《河畔人家》是家军以冀中平原白马河为题材创作的一部极具代表性的长篇乡土小说,它立足于白马河这个特有的地域环境,给读者呈现出的是一幅多姿多彩且富有浓郁乡土气息的生活画卷。
《河畔人家》的内容是丰富的,其艺术特色是个性化的。而家军那叨家常般的叙述方式更是冷静的、机智的,具有农民式的风趣,有强烈的地方性。
家军和乡村有一种与生俱来、血肉相连、无法割舍的情结。他的故乡,万物愈灵愈美。白马河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珍藏着他童年的回忆;那里充盈着他甜蜜的温馨;那里尘封着他儿时的玩具。家军生在农家,长在乡村,与生俱来的“草根”禀赋,培养起他对乡风民俗的浓厚兴趣,好歹要留下一笔。
因为,白马河,是家军的魂灵。
白马河两岸泥土的芳香对家军来说刻骨铭心。他就是白马河的歌者,白马河就是他的的精神家园。白马河的乡村生活,不乏故事性,那浓浓的乡音乡情,美妙的童年记忆,难忘的乡村往事,这些都是家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素材。这些生活故事,常常又会勾起他无限的乡愁,进而激发出他对故乡抒写的冲动。
这些故事,都是家军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真实故事。
家军立足于白马河,白马河畔的乡情亲情、野草禾苗、衣食住行、喜怒哀乐、音容婉貌,其信手拈来,有鼻子有眼儿,且能娓娓道来。家军好像啥都知晓,给人的感觉,一会儿像个须发飘飘的老者,一会儿又像个调皮的顽童。
家军在其在作品中描述的乡村星月,荷塘春风,如今早已渺无踪迹。那些曾经活跃在乡村的木匠、瓦匠、铁匠、鞋匠、焗锅补碗匠、阉猪、接生婆子、碎烂头发换娃娃的小贩子、卖熏鸡的……那些旧日乡村最后的手艺人的尊严与梦想,都在他的笔下一一复活。他把身边的每个人、每件事、每块泥巴都写活了,让你捧读时欲罢不能。
这是一幅世像百态图。
秉灯夜读家军的《河畔人家》,一股浓郁的泥土气息便扑鼻而来。那一个个乡情浓郁的真情故事,一幕幕风景迷人的乡村美景,一个个鲜活善良的乡民形象跃然纸上……读之如沐春风,如与故人相晤。
杀猪,曾是农村一道风景,既有惊恐,又有乐趣。
杀猪的时候,村里的大人和小孩子们都愿意来凑热闹,那场面应该是很壮观的了。农村有句话说:杀猪杀屁股。都是杀猪,家军却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捧出了一篇好文,活灵活现的把个农村杀猪场面摆在读者面前。
展卷玩味,那一个个熟悉的场景,无不仿佛黑白电影一般,一下在眼前鲜活起来。要杀猪,就要先抓猪,抓猪的开篇就很热闹,并打下了浓重的底色:后生们一进到圈里,就都猫着腰向猪扑去。圈里的猪一瞅玩真的,它可不干了,扯嗓子哭嚎起来,那声音能传出去二里地远,它跑着、跳着、叫着……
任你喊破了天,也无济于事了。
后生们一拥而上,揪耳朵的,扯尾巴的,拽腿的,按脑袋的,七手八脚把猪按倒在地。可叹这二百来斤的庞然大物,被几个后生死死按定,只有嚎叫之声,而无反抗之力。在按倒了猪后,后生们麻利地把它四条腿捆起来,扔出了猪圈。到了猪圈外面,有人递过来棵木头杠子。后生们把木杠子从猪的身子空隙里穿过去,两边的人嘴里喊着号子:起。就把猪抬到了矮桌子上。
猪,垂死挣扎,四脚乱蹬,嘴里发出“仰天”的嚎叫声 ……
这样的文字,读来真是饶有趣味,过瘾至极。我不得不佩服家军的笔力。他以白描手法勾勒物事,笔触平实朴素,没有大开大阖、浓墨重彩的渲染,虽笔墨繁简不同,然一经点染,则神形毕肖,活灵活现。
显而易见,家军童年时肯定是一个非常细心、敏感的孩子,也亏得他几十年过去了,还保持着这份童真、童趣。正是他的那些珍藏,唤醒了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找回了迷失的自己。
猪,逮住了,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此时,二牛子粉墨登场了:瞅见了凶神附体的二牛子,猪嚎的更欢了。二牛子不管这些,他让人把猪摆放好,在吩咐尔透旸拿个大盆放在了猪的脑袋下方后,狗日的眼都不眨一下,手里那把磨得锋利的牛耳尖刀一顺,使劲儿的朝着猪的脖子处捅了进去。狗日的忒狠了,长刀拥进,直没把柄处。二牛子稳定片刻后,才缓缓地将长刀向外抽出,即将抽完之际,猛听他大吼一声:端盆子接住了。说话间,刀一拔出,猪体里的血便喷泉般涌出来,咕嘟咕嘟的流到事先准备好放了盐的那个大盆里。
二牛子杀猪,拽不倒一边捧臭脚:好刀法。
猪,尽管喊破了喉咙,叫破了苍天,也摆脱不了被屠杀的命运,家军的这段文字中透出的那种令人伤感的宿命色彩,直击人心。家军囿于一个孩子的眼光,行文中没有插入任何成人的思考,他依然从一个乡村孩子的眼里去看那个世界,哪怕看到的是纯净和不解。
看得出,家军不想留给人们一个被改造过的“历史”。而他这种酣畅淋漓的写法,确实也让我读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风有雨有幸福也有痛苦的乡间,不仅有了湿漉漉的线条分明的轮廓,还有了那么一点隐隐绰绰的魂魄,我想,只有和乡村有着血肉般连系的家军,才能写出这样亲切自然、充满了幸福感的文字。(周静华)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