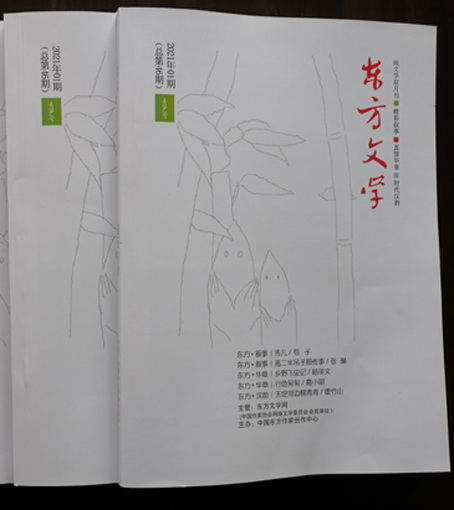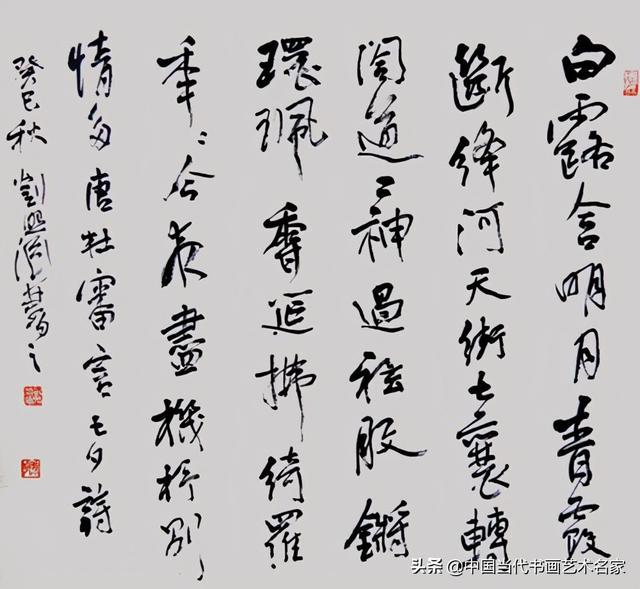1, 奇怪就从一株古银杏开始。
一条300米的通往大树之路,与一棵树的情缘纠结在岁暮。似云似雾的记忆,重叠在同一时段、天气、地域、尤其是心境之中 。这使我感到有些蹊跷,有些绕不过去的回味。它们为什么突然在我的面前重现?
恬庄是个平凡而古老的江南小镇,有一株这样的硕大高耸的银杏,矗立在郊外的野地上,谁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我看到它的时候,季节并非绿叶葱茏的春夏,亦非黄叶满地的深秋;每次都在岁暮,且已是三度重逢了。看到的是一株别样的、无可类比的、沉浸在阴霾的雾气之中的巍巍古树。它那撑天的枝干下矮上粗作婆娑状,估计有十丈之高。蓬隆的枝桠在下半部绕着一个梭子形,上面半株却如此的瘦削交错,挺立在寒风呜咽的天空里。它的年龄被疏枝败叶掩盖掉了,只有颀长的身躯露出了它曾经的伟岸。说它是耄耋之年不足为喻,它是一位千年的长者,俯视着一个青春少年。如何能在短短的五十年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叟?
某种原因使我始终没有走近它。我与它萧索地叩问,将透露多少个世纪的秘密?
少年时代的忧虑是因为离家的远,在异乡受够了冷漠、讥讽、嘲笑、自卑和过度压抑的穷学生滋味。一首《苏州的圆洞桥》多年后回味了这种复杂的感觉:
一座座跨不过去的古桥下,水的世界映出许多心灵的影子
把那些恍惚的表情,流淌到四面八方
梦,浮在水中的荷叶,哥德堡的眼睛锋利,抽刀断水、
把它们一次次地宰割、切半,挂上月亮的天空
那些个威严的长桥,它们会在顷刻之间崩塌?
桥身呵 ,咋出现了没有尽头的倾斜
从黑暗中陡然回首,尽显了桥孔中的放肆和自虐?
我的忧郁 走不出中世纪,那个神父悠悠祷告
而船家叫了,还有一座桥 哪里的水都没有固定的脚步
运走了许多船舶,却冲不走我内心的彷徨
水阻隔了的家乡 无数双鞋子、踩过一波波小事件
的涟漪,扩散、聚合、又陷于无形的裂痛
失重的魂灵呵,在蒙难。乌鸦一样黑幽幽的瞳仁
红黄色的喙嘴, 我的面孔被它激动和啄伤
与我的同学们和而不同的是平静下面的激流。他们或者就是漂浮在睡眠中的荷叶,我却是需从一个个黑暗的桥洞中穿行的过客。这条漂流在姑苏密如蛛网的河流上的、我的心灵之舟,要使它不歪斜、不倾覆、不碰撞,就需要一个船夫的准确观察力,和撑杆点水的拿捏本领。在天生嬴乏的不利环境中我往往被重度杀伤,或因一次意外的考分,或因一次与嬉皮士同学的冷然对峙。我必须保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的尊严。这是我的底线,也是我的一生行踪。现在想起来有点程度不同的、马加爵与他的同学们的“不等式”。他们能有被赞扬、被高挂、被羡慕的特权。一个穿了长可盖膝的旧衣、瘦弱的穷哥们,除了竟日饥饿的权利以外,被嘲笑、被挑剔、被戏弄,原来那时候就有的啊?
回家的寒假,汽车必过恬庄。
这地方与我们沙上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在长长的解放前,那个虽距离不过几十华里、而仄逼得找不到与之牵连的瓜葛地方,统统就被沙上人俩字以括之:江南,以别于本土。沙在海里、陆即江南大陆,距我们沙远着呢!旧时人们的世界观竟穿不透百里之遥的半径,当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的。我们看惯的是口音相同、穿着类似、风俗一致的同类同乡;对于圈外的乡土,哪怕离家不远的也有种不去想象之风马牛情结。但在儿童眼里,对人的观察有时是出人意外的仔细的。江南人到沙上小街无非三件事:卖淘箩筲箕、烂斩糖、香瓜西瓜。可见这三样商品为沙上所无,或沙上人不屑于做的。
想不到这样平凡极了的童年记忆,何以会在对树的一瞥之中迸发?丝毫没有情感之懈可击的家是一种贫乏,寄人篱下的继母家庭是一座冷冰的城堡。当我在汽车里陷入沉思,路逕恬庄首先看到这棵高大而又落寞的古银杏。我感到我们的境况类似,那座支离破碎无人光顾的苏州瑞光塔也是。通过三百米的距离我无法抵达它的真实。但能想象,古镇也有我幼时的卖筲箕淘箩、烂斩糖、和香瓜西瓜的江南人。有鲁迅语境中的鲁庄、鲁瑞、六一公公、闰土、长妈妈、阿q、小d、黄胡们?
既然我自己选择的苏州不能给我慰藉,而扔来一个个臭鸡蛋;既然家乡已经不外冷峻的现实,而张开了一个个故作幽默的冷酷表情;我的同乡似乎都在驱赶着我的情感。一个情感被掏空的幼体,是纸一样薄帩的,它不停地漂浮不时地寻找似一叶浮萍。一条细微的渠道就会潺潺的宣泄,一枝一槎就会轻轻的粘附。多年前的小贩与母亲联系在一起、课本中的乡趣与老街联系在一起。那株银杏在矮矮的夕阳里翩翩明灭,它背后的古镇在阴霾的气候中蹲躅。一个遥不可及的、只保留在我的心中的梦并没有逝去。古银杏是我找到的、认同的标志物,留下了贫贱时的孤苦的、忘却了原痛的呻吟。这就是我的300米回归的意义。这一条精神链接秘藏在几十年的游走经历里,促令我无意识构思恬庄的旧事。幻想八之十九、都是我的必由之路。
暗暗的、内心的沟通和融解,即是你的栖息。一株老树使我得到了体恤的安宁,这不是句谎话。
2, 第二次岁暮见到这株古银杏、它已纯属风烛残年了。你看,它那苍老的虬枝在风中再也发不出阵阵啸吟;那斑斑驳驳的树皮掉了下来,被人当做柴火;那飘落的扇形黄叶稀稀疏疏、盖不住它磨损已久的腿脚了。五十多年远去,在它的日历中只是1|16的概念。而我卑微的地位并没有实质的改变。为了远道客人的到来,饱尝了既要与他会面、又不能参与其中的尴尬。适可而止的与本地领导温庸的话语,需要人家明了未说出、而又不便的点明。不能与客人共度良宵的原宥,和隐隐的屈尊商量的卑下感;仅仅是他远道而来未提前招呼,我恰恰未被邀请和未出分文会资,而又必须与会陪客造成的。
备极寒酸,如此而已!
我笨拙的古道热肠,傻乎乎的带了礼品去会场找他。接下来便是陪同他参观风景名胜,适逢恬庄大兴土木,修建全新榜眼府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有何种必要?整条北街被翻得七翘八裂,只有绕道进入。就在那夕阳寒风飞鸟归林的时刻,抬头一望百米之外恰是那棵五十多年前的古银杏。此刻从里往外看它,与昔年从外往里看感觉是不一样的。一处人生驿站的凸出风景,矗立在灰色的雾霾里;榜眼府是它的殿背,迢迢古道勾划出了它的城府之深。据说该处原是座道观,亡其名泯其起讫年月,原配建筑早已坍圯有年不知所向了。恬庄初建于宋,此树估计距今已有千余年了?按树之身高腰围冠盖枝叶与之符合,则其珍贵也就不言自明了。
忽悟我们是老相识了!当我们的心灵颔首之间,它是沉默无语的。大约怪我蹉跎太久吧?初初算来,它至少经历过金兵南侵、蒙古铁骑蹂躏、元末的朱元璋和张士诚江南之战、清兵的江阴嘉定屠城、长毛时代的烧杀掳掠、日本兵1938年淞沪之战后的登陆,解放战争的上海争夺战、等等兵燹战火。然而它刚正不阿气节凛然,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地与人类周旋,始终保持了它的清明茁壮的本色。如今老了,更不在乎人们对它的态度了。
在它的眼皮底下,新一轮的喧嚣正在开始。傲慢与偏见、庸俗与浅薄、功利与价值,正在预见中不可避免的发生和反刍。在树的天空里,居高临下坚守着意志的坚韧不拔、芯质的诚挚朴素,依旧为古镇吐出源源不绝的芬芳,调节着一切来自地面的浮躁和不安。因为它知道,要从抽空了的恬庄、榨干了的恬庄再造出一处盛况,企图不减当年的胜景,简直是刻舟求剑,大大偏离了文化是由变革而发展的本质。已经毁灭了的旧恬庄、与颐和园的浩大工程是万牛一毛,曾经的辉煌属于皇族士大夫阶层。那六纵六横的井字老街被战争和运动焚毁;只剩下一条汩汩流淌的奚浦河,和一条双手能触摸左右店门的窄窄西街。一个废墟的重建、一个特定价值的恢复,是那么容易的吗?
在战争与和平迥然相违的错位里,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与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变成一对矛盾的双子座,在深空里发出冷冷的寒辉。它阻挡不了一朵新吹来的蒙昧之云,它担当不了一个文化黑洞的巨大陨落力量。我看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古恬庄,还不如说是个苏州古建集团的赝品展览橱窗。这里的赝品与许许多多拼资金、拼名人、拼豪华的古镇游,其实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文化空壳。在这里找不到论语的警句、尚书的星象、周易的变格、和老庄的逍遥。这种与自然与文化的割裂,又会有多少人来叩门领教呢?遗憾的是这仅是少数人的顿悟,多数人却在继续的疯狂。
在迷惘和惆怅中遭遇的一批批陌生人有着太多的曲解,为历史的进程埋下了令人叵测的伏笔。经过这轮古建大跃进,残破的东西、残留的遗迹、一切有着残存美的秦砖汉瓦、唐律宋韵都付诸东流了。眼前的一切岂一个乱字了得?我在车上与她、他、它们招手的时候,意味着与一个八百年古镇的告别。因为它如今叫新恬庄了。
愿与我的朋友诀别在古道西风瘦马,我的盼望也许太奢侈了吧?
3, 庞园数珍,是那个年代仅剩的实物模型。与轩丽的新榜眼宅相比,它算的上是柴门寒舍,形象之下多少有点落拓不羁。清康熙年间的蒋廷锡原来出自寒门,可以佐证。此居系庞氏末房长从蒋氏后人手中以二百两银购得。庞氏伯祖忠璐世居塘桥、系清末的探花,后投资围垦沙田聚财颇丰。续后三进旧瓦房前二进已翻新。临街的门面是1864年淮军与李秀成的常熟之战中,被广西长毛们焚毁后重建的。第二进是八十年代房主庞先生筹资翻建的。所以那《蒋廷锡故居》的控保建筑牌子,就悬挂在最后一进未改变的庭院门外。三进后面有古园一所。整个蒋宅现存面积八百多平方米。旧房之老在于它的矮和窄,与现在款式或许都是两个时代需要。
受主人邀请参观这所不大的旧园是我的福分。阴暗从上到下弥漫了庞园,众多的树木挤得阳光极难进来。在如此缺光的场所,植物们照常欣欣向荣。我看到了那些古老年代里生长着的藤蔓野草一代代不断繁衍。树木有青桐、桂花、六朝松、棕榈等;花木有木香、迎春、月季、腊梅、栀子等。盆栽花草更是数不胜数,点缀在前庭后院茶几长台之上。后园中倚墙而立的一株虎皮榆和国槐各领风骚两百多年,粗可两三握,是小园仅剩的古典精华了。那含苞初放的磬口腊梅、狗樱腊梅,播送着满园清香;在幽静之中可谓暗香浮动先得古园之春。还有两株粗大的广玉兰,绿荫冠盖高耸园空,却是改革开放后的绿化产物。要说庞园的特色,我看还是那爬满青砖围墙的常春藤、爬山虎、许些不知名的藤蔓,以及二三进之间的一口古井。藤蔓们如同蚯蚓一般,弯弯曲曲的从上到下一眼也不放过,寻找着可以攀援的毛涩棱角。感言于园主的巧心,把前后门槛上的藤丝扶正、任其生长。致使屋上屋下缠绕着细微如织的绛红、嫩绿、淡白等不同色彩的枝蔓之网。密密麻麻的生命之盛于此可见。而青石圈的古井亦是见证这所古宅的生与死的原物。汲水浇园泉眼清冽不减当年。
主人献茶,在那些虫蛀剥落的椽木栋梁,雨水浸蚀的灰砖望瓦下,有明清年岁的户牖花窗。有趣的是一张明式三条背榉木座椅。主人说,原有好几张皆被砍做柴火烧掉了,轻轻的一声叹息把蒙昧时期的憾意都隐没了。
当他要我发表意见时,可把我愣住了。我只是个门外汉。对于如何修葺这所袖珍园林莫衷一是。略说了一些不中肯的意见。边茶边谈中觉得,这座古民居的已经远离三百多年的万般读书高的岁月了。看不到那些蒋氏的国学精粹,也没看见现代百科和当代的林林总总。一个出了进士阁老的民居,因为书的缺席彻底与文化拜拜了!无可追梦的遗憾使我感到一阵透心之空。前后比较延伸开去,连现在的小学都迁到乡政所在地。生源大减,教育和文化的大量萎缩的后果,也许是这个经济时代的最大悬念。
世界的变化是必然的,世界的回放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千古定律。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里,古建筑的复兴只是原文化的一个虚幻的背影——它不应该被复活而只应该被提示。构筑在自然耕种经济之上的收租院的田庄,和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始的手工业作坊的恬庄,都不可能复兴了。恬庄是不能脱离自己的耕织时代的,否则它就不叫“田庄”了。我也曾经在故乡一步一声慨叹:那还是当初的故乡吗?这种无比坚定的冷却面世,只属于清醒者;热血沸腾的土地只属于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后生。在面目全非的事实面前,你没有犹豫只有承认。
21世纪会怎样?徜徉在恬庄“古”街,前不闻人声鼎沸的生活恬庄,后捡不到片纸只字的儒学恬庄。它只是一条按照今人设计的,比原界宽三倍高三倍的、徽式马头墙粉墙黛瓦的步行街、与一二所重建的清人故居的杂乱集合。使我悲哀的是,行人寥落的新街不过是一具古恬庄留下的尸体。即使用华丽的棺材来盛放,也听不到一丝有生命力的雪夜更柝之声,船只傍岸抛锚的嘲杂,和人头攒攒应接不暇的买卖场景了。找不到一个可以供笑话的人,闰土、杨二嫂、王胡、小d、祥林嫂、鲁四老爷、柳妈们的原型都远去了。充泝了这个外表华丽的装饰城的是小商店主,和老弱病残的少数留守族。源源不断的旅游队伍并没有应运而来。古街新造后恬庄还有什么意义呢?
被风干的历史之果业已凋零。灰蒙蒙的矮、窄、暗、深的格调原是它的本色,错将新桃换旧符的今日姿势,只是对一个空壳时代的反讽。然而只有那株古银杏的矗立,却依然坚持着一千年前的品行风度、是丈夫性的,与恬庄的官文化不相干,它不需要也享受不到加倍的呵护。
在寒风萧瑟中与我的古树挥手道别。崖山之后已无中国,崖山之后犹有宋银杏挺立至今。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