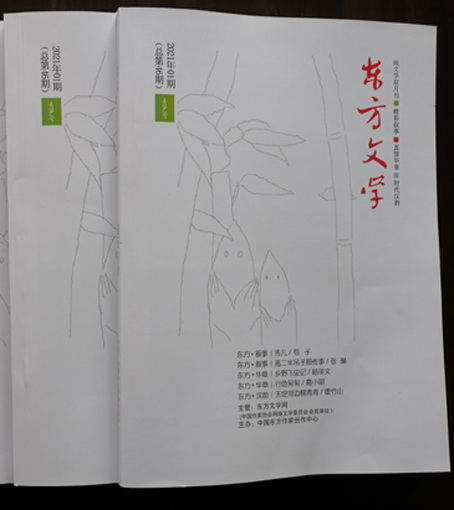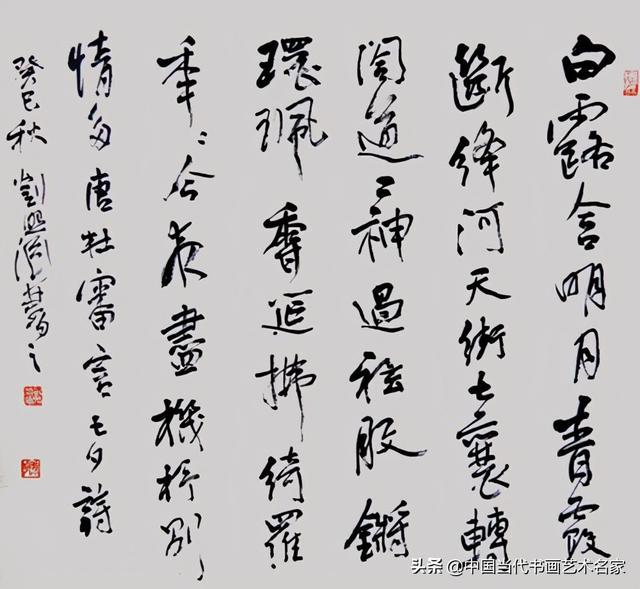大凡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走上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大都知道朱春雨。
因为他早年在长影厂当场记,60年代已有小说发表,与文学界多有交往。人到中年来到北京,成为一名专职军旅作家,声名鹊起,却又无头衔,大家就叫他老朱。
老朱算是英年早逝,走的时候还不到65岁。
那时我刚到皖南工作不足半年,记得是2003年12月12日那天,我在祁门的一个山沟里蹲点,接到宛柳电话获悉了这个不幸的消息,本想即刻返京送老朱一程,却不料那阵子台海风高浪急,请假未果。十几年过去了,我对老朱的思念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相反因为岁月的沉淀变得更加浓郁。
要说熟悉老朱,别说是二炮,就在全军也没有谁能比过我的了。
1978年春夏之交,解放思想的暖风吹拂着军营。
有一天,司办转来老作家冯牧给二炮陈鹤桥政委的一封信,推荐地方作家朱春雨。秘书交代,冯牧是陈政委在二野政治部工作时就相识的老熟人,后来入滇同在昆明军区,冯是文化部副部长,陈是军区副政委,工作中有过不少来往,现在冯老是文坛有影响的大人物,首长要我们认真研究提出意见。
当时全军专业创作队伍执行的仍是总参、总政1975年12月25日下发的“关于建立专业文艺创作组的通知”规定,二炮创作组编制员额8人,实际只有4人,其中画家3人,作家仅郭光1人,且年迈体弱,长年养病。我们文化部早就想充实新人,只是一时没有物色到合适对象,如今冯牧送人上门,首长意向显而易见,部里当然希望抓住机会促成此事。没过多久,领导就定下来了,要我即往老朱的工作单位吉林省通化市松江河林业局做一个外调。
临行前,我受组织委托,专门到朝内大街115号见了老朱一面,他当时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长篇小说《山魂》,还把和他在一起也是修改长篇小说的另一位作家冯骥才介绍我认识,就在出版社小院旧楼的一个房间里,是老朱改稿和睡觉的地方,我们在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从盖县老家到长影厂又到林业局,从他当乡里郎中的父亲到已在海军当兵的兄弟,老朱不仅给我讲了他的家庭,一再表达希望参军的迫切愿望,还给我讲了他正在修改的这部80万言的长篇小说,凝聚了他在大森林十几年生活的全部经历、心血和情感,他希望这个大部头能为那片山林和那些山民树起一座碑来,同时还想让这部新作成为他走进军营送给导弹部队的“见面礼”。这是我和老朱第一次见面,虽然过去素不相识,但他的真诚、热情特别是谈到创作时的冲动和激情,深深地感染了我。
接下来的松江河之行,依然保持并不断强化着对老朱的良好感觉。盛夏酷暑,山里却透着凉爽。林场没有楼房,家家都是用整根的圆木砌成的木屋,门前都堆放着码得整整齐齐的柴火垛,空气中弥漫着很浓的松油味儿。从林场领导、机关党委到老朱工作的宣传科,我挨个儿谈了一圈儿,还查阅了他的档案,最后作了家访。老朱的爱人李春岚是林场医院放射科的大夫,女儿苗苗已满9岁,儿子小莽不到5岁,尽管老朱长年在外,春岚一个人拉扯俩孩子,但她却很理解老朱在外奔波也是为了这个家。外调进行的很顺利,大家都说了不少好话,只讲了老朱一个缺点,就是遇事沉不住气,容易着急上火,说话不把门,经常得罪人,但我也从中感受到了山里人的正直、善良和朴实厚道。
回到北京,即向部领导汇报,接着起草“特招”老朱入伍的正式报告。层层审批,由夏入秋,等老朱穿上军装,已是1978年岁末的隆冬时节。
翻过新年,南疆燃起战火,我军被迫自卫还击。总政文化部组织全军作家艺术家赴前线釆访创作,二炮定下我和老朱、宛柳三人前往。当时老朱正在友谊宾馆参加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赶到宾馆找到老朱说明有关情况并征求他本人意见,老朱听后不容分说就去找出版社领导请假,回到房间拎着包就和我一起回到机关。经宛柳父亲协调,隔了一天的清晨,我们仨紧急搭乘西线总指挥、昆明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的专机赶赴昆明。先去见军区文化部部长毛逵,他在长影厂写《英雄儿女》时与老朱有过一面之交,经他协调,二炮釆访组去红河州,宛柳到主攻方向河口的野战医院,我和老朱去右翼金平一线的独立师。虽说我和宛柳当兵比老朱早几年,但上前线也都是头一回,我们都铆足了劲儿,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切实感受一下战场的气氛,力争能够写出像回事儿的作品来。
两个多月,我和老朱一头扎进藤条河畔的山林树丛,跋涉在界河两岸的野战营地。从师长到战士,跑遍了所有连队,釆访的官兵不下200人。每当夜幕落下,老朱就在帐篷的马灯下开始写作,最终完成了他的战地报告文学系列《朝着枪声走》《特别纪录》《中华瑰宝》。宛柳则独自沿河口边地向西釆访到文山,写出了短篇小说《小牛子》。这些饱蘸英烈血迹,浸透官兵深情的作品,都在全军“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征文中获奖。
在告别金平的前一个晚上,老师长在帐篷里专为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又是隆重的仪式。他拿出一瓶自己珍藏多年这次专门带到前线的茅台酒,倒在每个人喝水漱口兼用的绿皮茶缸里,外加地方慰问送的好几个午餐肉、凤尾鱼罐头,还有炊事班搞的炒鸡蛋和炸花生米,这在当时已经相当奢侈了。老师长当过贺龙元帅的警卫员,平时话就不多,他致祝酒词也只说了两句,一是咱这个大老粗不比你们作家能说会道,今天要说的话都在这个缸子里了;二是代表那些牺牲了的战友谢谢你们来看他们写他们。话音未落,就见他把一缸子酒咕咚咕咚全倒进嘴里了。
老朱从不喝酒。此情此景,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激动得按捺不住,老朱哪能例外,容不得多想,就端起茶缸往嘴里倒。好酒和义气,就像干柴烈火,在老朱心里越烧越旺,满脸通红,浑身发烫,自己给自己又倒上一缸子酒,向老师长话别。我原想拦一拦,但见老朱非常激动,额头上的汗水和眼角的泪水流在了一起,说了很多话,但决不是以往在城里机关的那种客套,我至今也忘不了老朱说过的那些掏心窝子的话:“我40岁时,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当了兵,一个不折不扣在南疆听见枪炮声的兵。我是在我的耳边时常听到厌烦大兵的言语中,当了这个兵的。可谓是一桩最不时髦的举动。但我是绝不后悔的。因为能在阵地上度过两个月的时光,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在这里,我补了我人生的课,也寻到了我心中的珍珠。假如我能把我在这里看到的表现出十分之一,抑或是百分之一,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大时代中的这样的兵,对于我都是慰藉和幸福。目睹战场,我怀着这样的激动,要告别这里,却久久地不能离去。是依恋?是感慨?不错,我与官兵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我的获得却非感慨可以系之,将作用于我今后的人生。”
5年之后,老朱重返南疆,又在前线度过两个月的时光。他对战争、对军队特别是对在改革开放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军人的认识更加深刻。恰逢迎来国庆35周年,二炮领导决定安排老朱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大阅兵的观礼。我给他打电话,经过好一番周折才联系上,他当时还在老山的猫耳洞里,说那儿的气温高达40多度,每个人都张大了嘴巴喘息,衣服又酸又臭,能喝一口从山下深谷里背来的凉水,就是最大的享受。观礼就不去了,他要和老山的官兵们一起在阵地上过节。半个月后,我收到老朱从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寄来的信,字字句句充满深情,其中有一段这样写到:
有什么能比战争更精确地检验一个民族的情操、能量和创造力呢?嘲笑过大头兵只知服从的青年,一旦他自己成为我们军队中的一员时,居然可以以流血乃至牺牲的代价,去做执行命令的楷模。战士接到家信,得知父亲买了一头小牛,或是富裕了的日子改善了妻子和母亲的婆媳关系,他可能已经躺在死神的掌上,可是他微笑了,是不是因为看见我们的明天?倘徉在TNT气味儿饱和了的巨石之间,抚摸数不尽的弹痕,忍耐难以排遣青春活力和偏僻环境相冲突而产生的窒闷,一声鸟鸣或一声狗叫,都可以诱发笑声或警觉。战士,是这样无声地深情地热恋着生活,不可言喻的自豪和缱绻交织的网络,漏出的是卑微渺小,留下的是崇高纯洁。正是这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追求的年轻公民组成的集体,建树着标示我们中华民族公德水准的丰碑。
然而,我真正理解了老朱信中的这段话,却是在读了他的新作《亚细亚瀑布》之后。这是老朱从猫耳洞里带回来的重要收获,但它又不像已有的一些同类题材作品拘泥于“战壕真实”或满足前线与后方的一般联系,而是从狭小的壕沟辐射出去,也不受军营的局限,纷纭万象,交叉纵横,打破传统的战争题材长篇小说的结构模式,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在现实生活和哲理思考的落差上层层架构的宏大叙事。但更让我受触动的是,老朱参军5年,两次抵近战场,每次都在阵地上度过两个多月时光,这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确实是不同寻常的经历,而对老朱这个新入伍的老兵、兼顾文人的军人更是难能可贵。他在创作这部无愧军事文学荣誉的力作的同时,自己也从这无拘无束倾泻的“亚细亚瀑布”中受到灵魂的洗礼。
当时导弹部队文艺创作室仅有四人,三位画家,一位作家,老朱真的是撑起了“半壁江山”,一个人扛起文学创作的重担。短短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所有的导弹基地,先后写出了《请看那盏灯》《沙海的绿荫》《大地坐标上的赋格》《深深的井》等一批反映在大漠深山坚守使命的砺剑人生活的作品。从题材来看鲜为人知,老朱揭开了战略导弹部队神秘的面纱,开辟了军事文学创作新的领域,在二炮和全军都拔了头筹;从人物来看别具一格,老朱致力写自己熟悉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与以往军事文学中的“大老粗”或“知识青年”的形象明显不同,自然比他人略高一筹;从内容来看走心入魂,老朱跳出了操枪弄炮、摸爬滚打的框框,着重对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广泛深入的审美评价,并把这些作品冠以“道德见闻录”,这在全军是第一人,无疑为新时期的军事文学带来了新的气象。荣誉的花冠开始向老朱开放,《当代》《十月》《昆仑》等大型期刊的作品奖,解放军文艺大奖,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接踵而至,同时部队对他嘉奖不断、记功从三等到二等,不要说此前二炮从未有过,就是全军的同行也投来羡慕的眼光。那段时间,老朱一直处于精神亢奋的状态。我们两家同住一个院,办公也同在一个楼,几乎天天见面,而每次见面都要听他滔滔不绝的叙述文坛见闻或绵绵不断的创作构想,他身上那种兴奋和自信给人以强烈的感染。
但是,当耀眼的光环渐渐褪去,老朱在创作上陷入了一个苦闷期。客观原因是,文学界对老朱作品的评价,显然不如对那些和他同代同龄的地方作家那样高,他有时会因此觉得有些被冷落。主观原因是,老朱的一些小说可读性不是很强,读者群受限,社会反响自然也不会那么强烈。坦率地说,文人相轻的“职业病”,老朱虽未能完全免疫,但他还有着“文人相亲”的优点,我多次听他讲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冯骥才、刘绍棠、张贤亮、高莽、徐怀中、叶楠、周涛、朱苏进、刘亚洲、刘兆林等作家的作品,而且经常流露出对这些作家的敬意。这段时间,表面上看老朱的精神有些蔫儿,但他骨子里并不服气,有时见到熟悉的朋友还会发几句牢骚。可能我是听老朱发牢骚最多的一个人,除了他对我的信任,还因为他讲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有的认识或知道一些,但我并不完全赞同,也没有一味迎合,恰恰是在我们俩之间开诚布公、直言不讳的进行交流。老朱年长我13岁,军龄却比我短8年,文学上他是老师,行政上我是领导,私下里他称我为小弟,把我看作是他在部队中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之间无话不说,有时激烈争论互不相让,有时老朱因为自我感觉过好导致不能正视自己创作中的不足,有时又因为我官升脾气涨对老朱说话简单生硬,几次把老朱一个年近半百的大男人搞得哭鼻子,但我们彼此都能了解和理解对方的心思,即使有时吵得不欢而散,但很快又能重归于好。但为了帮助老朱尽快消除精神上的苦闷,把创作状态恢复到最佳程度,我和他一起商量了一个到大型号远程战略导弹部队深入生活的计划,当时二炮的司令员、政委均作出肯定的批示,所有的装备、阵地和洞库都对老朱开放,首长希望打开这扇厚重的铁门,也能打开老朱的眼界和思路,让他对导弹部队生活有一个更新更深也更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出他的创作灵感和为砺剑人著书立说的使命感。我把手头的工作也暂时搁下,专门陪老朱一道走向人烟罕至的核武部落,同时还去探访部队驻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老朱生性好学,知识面很宽,一路走来遇到的新鲜事不少,凡事都爱刨根问底,弄出个子丑寅卯。我们俩就这么在大山里转悠了一个多月,回京的前夕,老朱与我作了一次很正式的谈心。出乎我的意料,他除了讲这次下来的感受和体会,还坦诚地分析了自己创作上有“三个不足”。一是先天不足,中年入伍,半路出家,而徐怀中、胡石言、叶楠、周涛、朱苏进他们哪个不是从战士到作家,自己缺了当兵这一课,而这种体验对军队作家至关重要,就是现在补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补得上的。二是主观不足,读书不少,经历坎坷,但对人生积淀提炼不够,认识转化也不够,像王蒙、李国文、从维熙、张贤亮很多地方作家都写出了个人和家庭的悲欢离合,自己也有相似经历,却未能写出相应的作品。三是条件不足,部队特殊,导弹部队尤为突出,有些东西敏感不好把握,不像写传统步兵和写边疆那样自由,现在还有不少约束,写起来放不开手脚。老朱说完这些,又叮嘱我两点:一点是刚才理出的这几条还在思考中,不一定都对;另一点是要我不外传,主要是担心传来传去走了样引起别人误解。我第一次听老朱这么坦诚地讲自己的问题,对我的触动很大,也启发了我的思考,事后还向领导作了认真汇报。
老朱走了这么多年了,那次也是我们俩最后一次一起下部队,特别是老朱对我说的那番话,什么时候想起来都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在我们部队和文学界,很多认识和熟悉老朱的朋友、同行,其实并不完全了解这个人。的确,他有时对文坛的个别作家不服气也说过一些气话,有时在一些有关待遇的具体问题上发过一些牢骚,有时对文学评奖的是是非非看得重了一点,有时还会在电话里给朋友抱怨生活对他的不公,其实,谁又能没有缺点呢?只不过老朱不加掩饰都把它表现出来了。当你真正对他有深入的了解,就能感觉到老朱的正直和善良,他是那种让人一眼就能看得透且不用费劲琢磨的人,他还是那种不会掖着藏着在背后鼓捣人的人,骨子里还有着东北人的那么一种仗义,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对于部队中一些有困难的年轻干部战士,经常慷慨解囊施以援手。至于老朱博览群书,多才多艺并且熟练掌握俄文还能翻译作品这个特点,大概在文坛不会有太多的分歧而得到认同。对于老朱这样一个优点缺点都很明显的人,导弹部队上至司令员、政委,下至司机、炊事员和站岗的哨兵,都是一样的尊重他、喜欢他,即使他有了什么过失,甚至在外界看来有些比较重的问题,从领导到群众还是一如既往地宽容他和爱护他。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很赞同王蒙同志在纪念文学前辈林默涵时说过的一席话,回顾历史,不是要爆谁和谁有什么鸡毛蒜皮的摩擦之“料”,也不是去争论他们之间的飞短流长,而是要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继承他们的奋斗和理想。
从部队回京后,我和老朱专门给政治部领导汇报,隋永举主任和王洪福副主任一起参加,这本身就是超常的安排,他们对老朱的收获感到非常高兴,对他在创作中的苦衷也表示理解,并且带着感情对他说,你到部队时间还短,有些东西一时不熟悉不了解写不到位也正常。干你们这行,讲究一个瓜熟蒂落嘛!我们对你有信心,你自己也要有耐心,更要有恒心,凡事讲水到渠成,干成事干大事还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两位领导还提出,老朱情况特殊,在创作上可以适当放宽一些,一方面要多下去补补课,另一方面要把过去的生活积累调动起来,人生是一笔财富,无论在那里写什么,只要写好了,官兵爱看,部队有益,就是合格称职。
自那以后,老朱的思想包袱慢慢放下来了,情绪逐渐调整恢复。在这个阶段,用老朱自己的话说,“久久彷徨于文场的热闹之外”,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用于新的创作,先后写出了《橄榄》《血菩提》两部长篇。前者被老朱称之为国际题材,写了中、俄、美、日四国中多个家庭几代人的沧桑,并且运用多种创作手法,将不同民族的典型人物、情节细节和带着荒诞色彩的故事交叉叠印,表现了他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深度思考。后者则是老朱耗时三年半,成为他创作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还有一个副题“浪漫的满州之一”,或许一个更为宏大的创作构思正在他的孕育之中。记得他对我说,写《橄榄》时尽其所能做了一些人类文化人格的横向比较,书出来后又觉得意犹未尽,还想继续推开沉重的历史之门纵向地去看看过去。看起来他是在讲述20世纪30年代长白山深处抗日联军、山林土匪和日本侵略军浴血厮杀的故事,实际他是调动一生的积累写自己的民族和故乡,通过文化寻根考察满族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优长与劣根,其丰厚的内在意蕴,显示出整部作品深沉的历史感和现实的文化意义。
《血菩提》为老朱赢得了新的荣誉,不仅获得满族文学奖,还得到文学界好的口碑。此时已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记得当时老朱给我说过他的一些感受,把本该放下的事存在心头,真的会让人付出代价,那些代价可能是生气、沮丧和愤怒,甚至是更糟糕的感觉。现在有些明白了,我们真的负担不起那些不断付出的代价,我们越快学会放下情绪负担,就能给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留下越多的空间。部队为了褒奖老朱取得的成绩,决定将他的专业技术级从5级调至4级,同时批准享受政府津贴,这表明二炮领导始终没有责怪过老朱而对他另眼看待,相反一直把他作为特殊人才高看一眼给予特别的关爱。
或许因为老朱日以继夜的创作耗费了太多心血和精力,或许因为看见深入改革的矛盾和社会现实问题叠加而忧国忧民的心思太重,再加上他原本血压就高,性格急躁,长年抽烟,生活又不规律,不久就因突发脑梗而入院抢救。当我赶往医院时,他已不会说话了,睁开眼睛一直盯着我,嘴角不时地咧一咧。看见他漠然的表情,我不知道此时该说什么才好,只是坐在靠近病床的椅子上久久握着他的手不愿松开。万幸的是因治疗及时,老朱的记忆力开始恢复,慢慢地可以认人了,后来回家也恢复了一些简单的生活能力,但情绪一度有些低落,他的创作基本上从这个时候停顿了。部队领导和机关的同事对老朱的健康状况十分关心,李旭阁司令员、隋永举政委、隋明太政委、王洪福副政委多次到家中或医院探望,李司令的老伴耿素墨大姐还专门邀请并陪同地方名医一起上门给老朱诊病,给他以心理安慰。军队的作家朋友更是对老朱的病情十分牵挂,徐怀中部长多次打电话了解病情表示慰问,还专门叮嘱我要多多关心老朱。京内外的作家利用参加作代会的时机,相约一起到家里去看望他。那天我也在场,数了数共有十七八位,都是当代军旅文学的中坚,场面温馨感人。好像在军队作家中,还没有谁在本人活着的时候,一次能有这么多的作家自发地、由衷地而且是带着感情到家里去看望。老朱真的是被感动了,他当时说话还不利索,止不住地一个劲儿流泪。
2003年非典过后,我被调往皖南任职。离京前,我到家里去和老朱话别。虽然看上去他的身体还是虚弱,但精神尚可,得知我调动的消息,指着墙上挂的几对竹简对我说,这都是我从皖南带回来自己刻的。我走近仔细打量,一劈两半的竹筒经过简单打磨,刻着老朱书写的古典诗词,然后又上了一层清漆,虽说工艺有些糙,却另有一种拙朴的味道。我在赞叹之余,心情反而感到有些沉重,对于这样一位文思敏捷多才多艺的优秀作家,64岁是正当年呀!偏偏生了这样一个病,欲写不成,欲罢不能,病痛尚可忍受,精神折磨却让他苦不堪言。那晩我在老朱家里坐了很长时间,当我不得不告辞的时候,他非要坐着轮椅把我送到电梯口,尽管走廓里光线有些暗,我却能看见老朱的眼圈又有些红了。
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深夜的辞行竟成了我和老朱的永别。不到半年,2003年12月12日,老朱因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永远离开了我们。听他儿子朱莽说,其实父亲早有预感,总觉得身体快不行了,后悔自己当初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十几年过去了,去年岁末的一天,我和春雨当年的几位老朋友缓平、申煊和业勇一起来到八宝山,在搁放老朱骨灰的墓墙下,深深躹躬表达我们的哀思。我对他说,13年前我没能赶回来送你一程,请老大哥千万别生我的气。你走了这么多年,我和宛柳经常想起你念叨你,你和我们的感情不会随着时间流逝,因为你一直都在我们的心上。我还告诉老朱,你活着的时候咱是二炮,现在改名火箭军了。你病重时缓平就接了你的班,后来他又白手起家创办了二炮军史馆,把你的照片连同你的作品都放在馆里陈列,说明战友们没有忘记你,导弹部队也没有忘记你。申煊现在已经是很有一些模样的书法家了,他说当年看你练字的情景至今难忘。业勇是你手把手带上文学路的,刚刚又获得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荣誉——韬奋奖,也算是不负你的心血吧!尽管那天气温骤降出奇的冷,但我们都在刺骨的寒风中默默地伫立,望着镶嵌了老朱照片的墓墙久久不愿离去。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