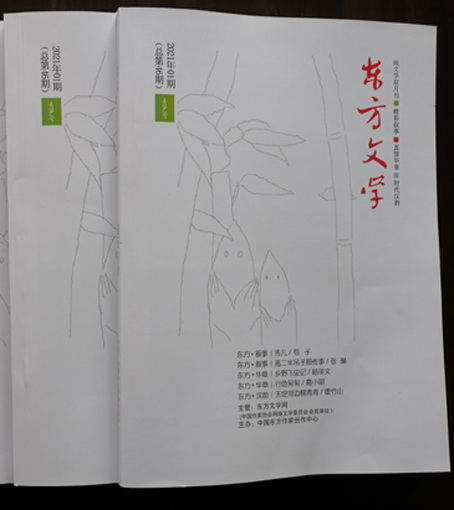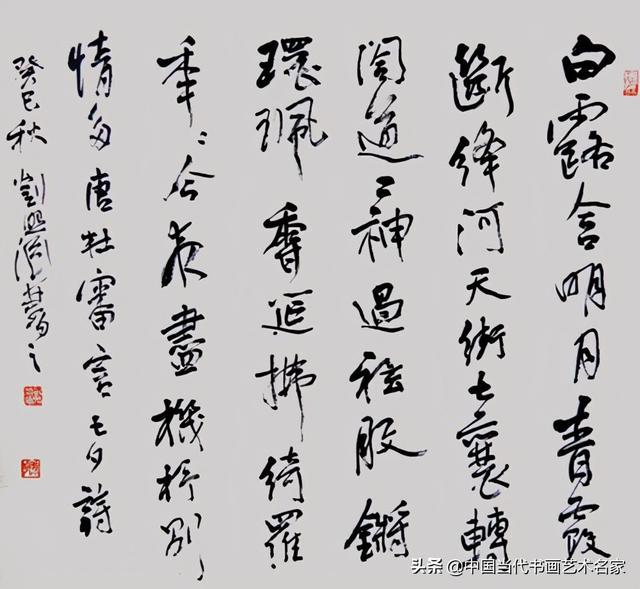我的生命历程可以说与一条大江息息相关。
我的出生地就是依偎在黑龙江畔的一个小村庄,她的名字富有兴旺发达之意——兴隆,是生意人最喜欢的字眼。
我的故乡——黑龙江畔,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黑油油的土地,十分肥沃,种啥长啥,夸张一点说,插根筷子都会发芽。这里是东北地区典型的鱼米之乡。所以说,在闯关东的年代,我的曾祖父千里迢迢选中了这块宝地度日。于是,我家的祖祖辈辈在这片黑土地上繁衍生息。我的曾祖父、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父母都在黑龙江畔入土为安。
我是喝黑龙江水长大的,那时村里就地凿开的水井里的水,都是与黑龙江水相通的,井水的张落与黑龙江水的起伏同处一个水平线上。那井里的水很清澈,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天,“咕咚咕咚”畅饮一番,拔凉拔凉的,且甜丝丝的,绝对有解暑降温之功效。
我的欢乐的童年,除了在教室里读书外,一年春夏秋冬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嬉戏在黑龙江畔的。我和童年的小伙伴与黑龙江结下不解之缘。开春,在黑龙江边挖过野菜吃;盛夏,
下到黑龙江的浅滩里,浑水摸鱼,燃一堆篝火,吃烤鱼,真是人间美味;老秋,爬上江边的山里红、稠李子等野果树上摘野果子,吃的嘴唇发紫。在那饥饿的年代,黑龙江丰富慷慨的馈赠,以解我们的饥肠辘辘。可以说是黑龙江养育了我们的生命。在北方漫长的冬季,那时的小孩子没有更多可玩的东西,我们就踩着皑皑白雪,来到冰封雪裹的黑龙江江面上,抽冰尕,坐在小爬犁上溜冰,顺江坎往下出溜滑雪。看大人们用冰镩凿冰窟窿捕鱼,看见冰面上活蹦乱跳的鱼,我们也跟着欢呼雀跃。那欢快愉悦的情绪,驱散了周身的寒气,好像不是身在寒风凛冽的严冬。
在我所住的屯子往北有一个黑龙江的支流,我们都叫它北大沟,再往北不到5里路就是黑龙江主航道。紧靠江边有一座不足50平方米的土草房,当地的人们都叫它兴隆鱼湸子,是江边打鱼人临时住宿的地方。我们屯里的这些半大孩子,一放暑假,就成帮结伙的往那里跑。或在江边垂钓,或到浅滩处抓鱼,或到树林子里找野果、野菜、蘑菇什么的。
记得小时候,常常盼着去黑龙江捕鱼的外祖父满载而归。外祖父一到家,我就立刻围了上去,仔细看看外祖父又打到什么鱼了,都多大。外祖父在黑龙江上划一个三板子船捕鱼,他总挑大的捕,因为他使用的鱼网网眼大,小一点的鱼都是漏网之鱼。所以我见到他捕回来的鱼基本都是3、4斤以上的鱼。什么大鲫瓜子鱼、大鲤子鱼、大鲶鱼、七粒浮
子,还有大鳇鱼等等。那时这里有“棒打獐子瓢舀鱼”一说,那时的渔民去黑龙江打鱼,基本都是打鱼打到满满一船仓才回来。打到的鱼多的吃不过来,实在卖不了那么多,或送给亲朋好友,或腌咸鱼、炒鱼毛。记得那年冬天,外祖父去黑龙江上用冰镩穿冰眼捕鱼,竟打出来好多二、三十斤重的鲟鱼,用爬犁拉回家放到仓房里冷冻着,什么时候想吃,就用铁锯锯下来一骨碌,待化开后,放在大铁锅里炖着吃,加上辣椒、大蒜和生姜等佐料,吃起来开胃,鲜美可口。尽管此事已过去好几十年了,但好像至今我的口中还留有那种鱼香,氤氲着我的周身不散,我仿佛常常闻到黑龙江水的味道。
我生在黑龙江畔,长在黑龙江畔,常常听到这里的老年人讲一些有关黑龙江的传奇故事,特别感兴趣,我往往听得入了迷。
我家村西不远处有一个大水坑,老年人都叫它老龙坑。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具体时间不详),天宫中有一条性情耿直的黑龙被贬下凡间。黑龙四处游荡,发现一处高台前聚集了很多人,他就化身为名叫小黑的年轻人,来到人群中一探究竟。原来这里久旱无雨,庄稼旱死了,人和牲畜都没有水喝,眼看着活不下去了,人们搭起供台,燃起高香,对着东南太阳升起的方向,每日哀告跪拜,祈求上天降雨。人们的头磕出了血,嗓子喊哑了,可是响晴的天空火辣辣的太阳,没有一丝的云朵。当黑龙看见人们无助的眼神,黑龙看不下
去了,他决定牺牲自己,拯救这块土地和这些善良的人们。黑龙盘旋到半空中,将身体弯成锥形,对准供台用力砸下去,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把地砸成了一个锅状的大坑,石头被砸得飞起数丈高,落下来又砸出无数的小坑。地下的泉水向上喷涌而出,不一会儿,整个大坑就满了。这时,黑龙将身体弯成拱形,如一张巨大的弓,随着一声巨响,黑龙头朝上尾朝下,将粗大的龙尾伸到水里,用力的旋转摇摆,将水绞到空中后撒向地里的庄稼。“有水了!”人们大喜过望,高兴地用柳条敲打水桶为黑龙助阵加油。
人们得救了,庄稼返青了,可是黑龙却又一次的获罪遭贬,被打入黑沉沉的黑水江,永不复出。为了纪念善良勇敢的黑龙,人们把这条黑水江叫黑龙江,黑龙砸的大坑就取名老龙坑。
这个水坑形状如锅,直径约有一百多米,以主坑为中心,方圆十里的湿地四周分布着远近、大小不等的几个小坑。主坑的深度没有人测量过,坑水随着黑龙江水升降涨落,但无论多旱的年头,坑水从未断过坑内繁衍着野生的草鱼、鲢鱼、鲫鱼等鱼类。
至今,人们都说,老龙坑的底儿和黑龙江是相通的,小黑龙在老龙坑和黑龙江中保佑着黑龙江畔的人们,让老龙坑的一草一木、一树一景都充满了灵性,散发着神圣的光辉。因此这里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除了老龙坑的传说,这里的老年人还给我讲过秃尾巴老李的故事。
一户居住在一条江边的李姓人家,有一位正值豆蔻年华的少女,一日在江边洗衣服,忽然狂风大作,一声惊雷,姑娘当即昏厥。事后腹部渐渐隆起。请郎中诊断,已身怀六甲。不日竟分娩出一条头上长角,身上有鳞,似蛇非蛇的怪物。李老汉一怒之下,手持菜刀闯进闺房,向怪物的尾部砍去,怪物尾断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只见一团黑雾,怪物腾空而起,落入黑龙江中。这就是那条黑龙,人称秃尾巴老李。
从此以后,江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老百姓安居乐业。但好景不长,一条白龙来此兴风作浪。黑龙岂能忍让,于是黑白两龙在江中撕杀起来,难解难分,闹得天昏地暗。当地老百姓念及黑龙往日的恩惠,纷纷前来助黑龙一臂之力。见到江水泛起黑浪,就往江里扔馒头。水一翻白沫,大家就一起往江里投掷大石头,砸向白龙。经过三天三夜激战,白龙已亡,残鳞败甲浮出水面。黑龙因伤势难忍,一跃腾出江面,跌落岸边草丛中,躯体弯成月牙形,身下砸出一条长长的月牙形沟壑。老百姓迅速围拢在黑龙身旁,一位郎中闻讯赶来,给黑龙包扎好伤口。人们怕黑龙因离水而死,纷纷从江中提水,浇到黑龙的身上。没用几日,黑龙养好了伤,恢复了体力,奋力打挺,飞向空中,一头扎入江水中。从此,再也看不见黑龙的踪影了。
老百姓为了纪念黑龙,把这条江取名为“黑龙江”。
在黑龙江流域,流传着许多关于黑龙江的美丽传说,衍生出许多动人的故事。我就是在黑龙江水的滋养下,并在这些美丽传说和动人故事的熏陶下,慢慢长大的。长大后,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走多远,我都没有忘记我的故乡——黑龙江。仿佛她与我有某种血源关系和深厚的因缘关系,如鱼水之情,血肉相连,那份难以割舍的情缘,将伴随我的一生。我参加工作的第一天,就去我的故乡那个黑龙江边境乡镇报到。四十余年,朝朝夕夕,我一直在这里工作,从没离开过这里。这种深情厚谊,难以言表。我愿意为她的源远流长,为她的繁荣富庶,不停地为她做着力所能及的工作。在我退休以后,还为全县在黑龙江上发展网箱养鱼进行各种宣传工作和起草相关汇报材料,同时不断收集整理她的历史资料,编辑她的传说故事,歌颂她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每当我来到这里,都会久久地伫立在地处北纬48°地带的中国第三大河——黑龙江畔,亲眼目睹她挟裹着额尔古纳河冰冷的雪水,翻滚着微微泛黑的浪涛,汹涌澎湃,波澜壮阔。无论谁站在岸边,都会感到有一种心灵上的震撼。它以恢宏磅礡、不可阻挡之势,向东,一直向东,奔腾不息,奔向更加广阔的海洋。
我站在黑龙江边,往往会流连忘返。我作为一名黑龙江人,特别是自幼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感到自豪。我会不由自
主、情不自禁地像呼唤生我养我的母亲那样大声向你呼喊:我爱你——黑龙江!你世世代代滋养两岸不同国度的人民,愿你永远伴随两岸人民共生共存共荣。
【免责声明:本站所发表的文章,较少部分来源于各相关媒体或者网络,内容仅供参阅,与本站立场无关。如有不符合事实,或影响到您利益的文章,请及时告知,本站立即删除。谢谢监督。】
发表评论
推荐资讯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