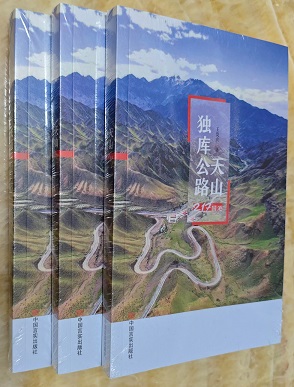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广西,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少数民族作家基本上用汉语创作,多数作家其实与汉族作家的题材和写作风格无异。但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还是力图唤起民族的文化记忆,从本民族或本地民间文学中发掘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资源。当然,由于当时特殊的文化政治氛围,作家常常将那些源自本民族的素材进行必要的加工,打上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像韦其麟的《百鸟衣》,即以自己家乡的壮族民间传说故事为蓝本,混融当时的阶级叙事而成。而在一批成长于上世纪80年代的作家笔下,多数已经不再关注民族文化记忆,而是注目于当代的现实生活,如鬼子、凡一平、李约热等人的作品,均可说是聚焦于一些普遍性的问题,如城乡关系的不平等、底层人民的困苦、城市各色人物的欲望与挣扎等。
在现在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身上,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甚至在壮族诗人费城眼中,民族语言与故乡的一切都呈现出与自身文化认同的格格不入:他在矿区长大,直到14岁才回到故乡,即他父亲的老家。那里土地贫瘠,道路肮脏,人们目光呆滞,更要命的是,人人讲壮话,而他觉得壮话“粗俗不堪”……语言的隔阂让他非常孤独。这样的经历和记忆,让他产生了重构故乡的愿望,他要用文字(当然只能是汉字)呈现“另一个故乡和村庄,以及内心的风景”。这反映了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写作中的一个共同倾向,即他们生活在一个面临同样问题的世界中,这些问题与民族身份无关,而与现代性的来临、社会转型有关。
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作家的文类选择上,上世纪50年代登上中国文坛的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大多以诗歌闻名,如韦其麟、苗延秀、包玉堂等,这可能与他们自小接受民族传统的歌谣文化的熏陶有关。而到上世纪80年代后,能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小说家,这是现代文学世界的文类格局的反映。现代小说,由于其容易阅读、故事性强,所以比诗歌更广泛地为读者和市场接受,当然也引来更多的作家加入虚构故事的行列,现在的广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自然也不例外。这些小说家写作的题材和风格多样,但多数来自农村或有乡村生活背景,他们的写作常常从泥土中吸收养分。陶丽群关注底层民众特别是乡村妇女的喜怒哀乐,描述他们在困境中的挣扎与努力,刻画他们的坚韧与牺牲精神。他们在艰难中谋求改善,在困苦中维护尊严。像《漫山遍野的秋天》中的三彩,人长得丑陋不算,无情的命运又让她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人,她却从不低头,她渴望做一个健全的女人,生养孩子。最后还算圆满的结局是一系列巧合和误会所导致,幸福总是需要运气的。周耒的小说,大多关注那些从乡村到城市寻找更好生活的男女,他们被迫在不熟悉的环境中拼命,有时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但他们并非生来就是坏人。《幸福来到陇沙屯》中的许树才叔叔,为了改善乡村贫困的生活,制作假烟,最后亡命天涯,却为村子里的其他人带来了命运的转机。他们承受命运不公平的安排,努力改变生活现状,自己寻找生命的快乐,就像《舞场》中的米莲,在废墟上起舞;当然也有人返回乡村,像《飞入天中的梯田》里的小菱。这些小说或许有各种结构上的瑕疵,却再现了作家对当今社会特别是城乡关系的复杂性的思考。
与前辈作家相比,这些青年作家非常重视叙事技巧,体现出非常强的文体意识,在制造悬念、运用平行或交叉叙事、颠倒故事顺序、留白等方面用功,使自己的文本更具张力。如潘小楼的《秘密渡口》,本是一个人们习见的悲剧,一个女人偷情怀孕,却被不知情的情人抛弃,又得不到丈夫的原谅,只好一死了之。小说却借助一个神秘的“水猴”传说,作为推动故事前进的悬念:丈夫既利用传说来遮掩妻子自杀的真相,也用来说服自己的不安,结果,自己几乎相信水猴真的存在,水猴变成了他的心魔。而19年后,负心的情人也被相好抛弃,后悔之余前来寻找旧情,却无意中得知一半真相,并解除了困扰丈夫多年的心结。作者自己成长于水泥厂的环境中,而今工厂停产,曾经生机勃勃的一切归于寂静,潘小楼将那种迷惘的心境化为自己小说的背景与氛围,通过想象力的发酵,通过文字的揉捏,生产出芬芳的作品。如果说潘小楼的小说常常由某种追忆形成,那么杨仕芳的《伤疤河的影子》则仿佛是在印证弗洛依德的“事后性”理论:一件事情并不是在它初次发生时完成,而是在其第二次发生时完成。吴春芝本来大有前途,却因为被村长强奸而改变了一生。当她认为已经用时间治愈了自己的伤口时,她又被两个男人强奸了。于是20年前的那个创伤时刻复活了,她想报复男人,但不是刚刚强暴过她的那两个,而是20年前的村长。但是,现在的村长已经不复当年的勇猛,变成了一个痴呆老人,而她也不是当年的吴春芝了。小说最后留下了一个悬念,即吴春芝的下落。她如果在伤疤河里死去,到底是失足,还是自杀?《秘密渡口》和《伤疤河的影子》都涉及河流中的女性死亡,提醒我们时间之流无法彻底冲走的创伤内核。在我看来,这一代的作家大多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所以他们的写作有时也会向前辈致敬,如杨仕芳《流逝》的开头,“欧元刚坐在32岁的夜晚里,头顶悬挂着一轮圆月。20年前的夜空,头顶也悬挂着一轮圆月。皎洁,孤寂,似曾相识”,月亮的意象是源于《狂人日记》还是《金锁记》?在继承和发展中,他们试图走出自己的路。
生在一个巨变时代,作家们在作品中再现生命的创痛,同时每每书写现实的离奇与无奈。黄土路多数作品的骨架都是一个荒诞的情节,如一个被心爱的女人拒绝的男人,为了每天见到她,竟变作了她家门前的垃圾桶(《垃圾桶》);一个被日常生活琐事搞得非常狼狈的作家得到一台可以洗去人记忆的洗衣机,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洗衣机》);一位被人出卖的副市长,住在小姐的子宫里才觉得安全(《谁在深夜戴着墨镜》);有一群人患了“多心症”,容易对别人产生感情(《赶往巴格达》);小伙子捡回的田螺真的变成姑娘,与他结婚,生活在一起(《桂村的田螺姑娘》)……但如果作家只写荒诞的故事,而不是通过这种荒诞揭示生存的真相,是不可能触动读者的。黄土路写的这些故事,与其说是写生活的荒诞,还不如说是写生存的无奈,更是写那些改变生活的愿望如何造成了相反的结局:“多心人”想赶往巴格达阻止战争的爆发,可当他们到达时,战争已经夺去许多人的生命;洗衣机让几个家庭成员改变了身份,同时让原先的家庭与生活记忆破碎,最后只好砍碎洗衣机;田螺姑娘并没有获得想象中的幸福,她不堪忍受村里男人的蹂躏,逃走途中又变成了田螺。
除上述小说家外,广西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中还有何述强、梁志玲、纪尘、黄芳、费城、林虹等人,在各自的文学园地里耕耘,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何述强的散文主要取材于亲身经历的人和事,他在那些草根写作者身上,寻找文学的根;在那些荒碑野坟中,寻找逝去的文艺英灵;在那些山野传奇里,寻找自己文学的灵感。《草根的呼吸》用深情的笔致描述一群生活在艰困之中,却对文学艺术不离不弃的底层文艺爱好者。他们中有的从事摩托车修理工作,在油污之中阅读柳永和辛弃疾;有的以刻碑为生,却不让穷困潦倒磨蚀自己的志向,写下“衣虽三寸垢,深处不沾尘”;有的是打工的农民,衣食不周甚至患有恶疾,却一直坚持写诗。在文章中,他写的多是无名的人、物与地,一块废弃的青砖,一块字迹湮没的墓碑,无端引发作者的感怀与猜想。诗人黄芳以自己的细腻敏感,书写对世界的发现,抒发对生命的感想,当然,还有,如她自己所说,“与事物的相遇”。当黄芳吟咏日常生活时,费城却将视线停留在了故乡,当然,这是一个重构的故乡。他的诗充满了一种紧张感,现在与过去、城市与乡村、现实与想象,纠缠在一起,纵横交错编织成一行行诗句,“伤口在病变中述说利刃”(《放牧灵魂之使者颂歌》)。
也许有人要质疑,这些作家都来自少数民族,为何很少书写少数民族题材?其实,这正反映了当今社会的现实,在整个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在社会生活里挣扎与奋斗的男男女女,时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必然会试图打开自己的精神世界,寻求与更多的人交流,而不是把自己封闭于狭隘的认同,或者,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记忆压抑到写作的无意识深层。在广西,民族杂居、文化混血,更使所谓纯粹的民族原质磨蚀消融。这些少数民族作家之放弃特殊性而转向普遍性的写作,也就顺理成章、情有可原了。他们用自己的作品,关注现实,或再现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或反映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或表达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执著追求,或书写人类心灵的点点滴滴,丰富充实着我们的文艺花园。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