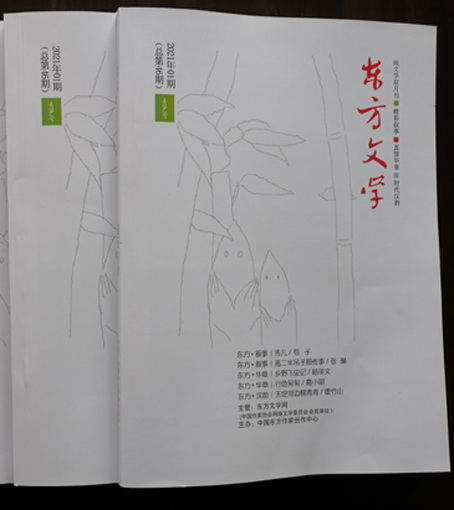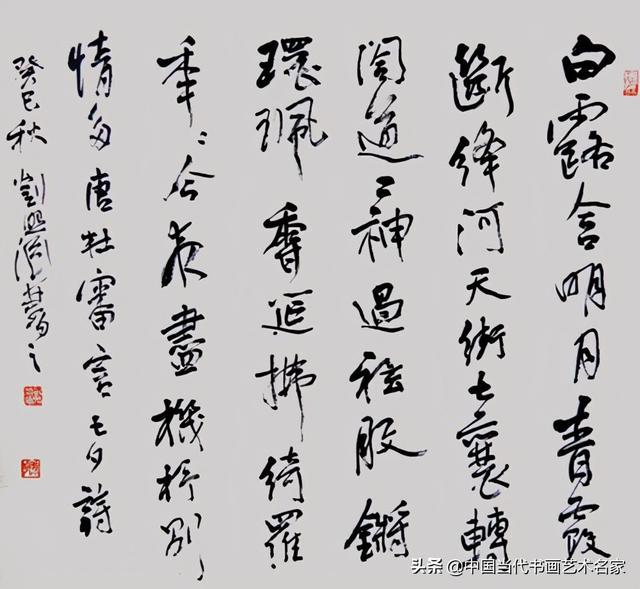20年前,我这个湖南人到了广东。我入厂打过工,在杂志社做过老总,然后有幸走进最基层的政府机关工作。我和同时代的人一样,面对这个浮躁的时代,无时不对生活有一种热望与内心纠结,渴望更多的知识来净化自己。尤其是文学创作中,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知识的严重不足,我文学创作的血脉已严重阻塞。但我工作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偏僻的小镇,离市区80多公里,文学爱好者不多,文学交流更少,我无法自我判断,我需要得到更高层次的学习。于是,我时刻盯着某个外出学习的机会。因此,我放弃了一份十分重要的工作,等待走进鲁院的机会。
2013年9月4日当我走出首都机场,阳光一直带着我来到位于芍药居的鲁迅文学院。
鲁院的教学模式,是一种敞开的模式。这里的课程不仅有文学,还有军事、科技等内容,课程涵盖更多的是一种为人为文的精神传播。“优秀的作家是文字的魔术师、炼金师和大师。”作家刘恒老师的课,我觉得不仅仅是一堂文学层面的课。他从人的生命、欲望、利益、竞争等创作动力出发,讲述文学、文字的创造和在这种创造中创作主体得到的精神上的解放与救赎,指出写作和我们认识自我能力的关系。他从创作实践出发,阐明了对文学关键元素的真知灼见。他认为写作是一个和自我作战的过程,是以文字、逻辑思维、虚构、想象力、风格等为武器的一场战役,而作家就是这场战役的指挥者。
科学家欧阳自远老师的课,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人类登月的那些精彩,更让我看到一个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对鲁院和对鲁院学子的尊重。年过古稀的他,上课时执意地要站起来上课。他说:“这才像先生。”先生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好久。先生是什么?是榜样的力量!我想能在这样的磁场里历练,何愁学不到知识?
在鲁院这个大“磁场”中“鲁二十”是一个温暖而快乐的集体。老钟是我们的班长,来自总政,曾获得过全军文艺奖。开学典礼时,他着两杠四星军装。军事知识极度缺乏的我,当时还一本正经地问道:“你是不是中尉?”想不到他是一个师级干部。孙大顺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姜大姐来自贵州,写小说早有名气,这个大姐后来还与我同桌两三个月。任海青曾与我同时在一家刊物上发表文章,她的名字来鲁院前我就熟知。霍君来自天津,斯文优雅,可小说写得特别棒,仅今年就发表了五六篇中短篇小说。我们6人年龄相仿,性格相近,谈笑间我们会不由分说地挽着手排成一排,唱着歌向院子里走去。月亮走,我也走,歌也跟着走。大顺会唱的歌最多,这个曾在部队生活了10年的人,会用歌声打发时间,而我没有一首歌能唱完,霍君会的歌更少。
我们每天都在讲述故事,我们也似乎每天都在演绎故事——因为我们都十分珍惜这场难得的缘分。走进鲁院,我就代表广东,因为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选送来鲁院学习的作家。从鲁院走出去,我代表“鲁二十”,因为我是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的学员。因为有了这个责任,我不敢造次。班里49个同学都融成了一体,我们像和和睦睦的一家人。4个多月的时间会很快过去,但我们的友谊会延续到永远,甚至我们的下一代。
施战军老师说鲁院是一个修心养性的地方,是看重人品的地方,是一个让作家自己慢下来的地方。而身处其中的我,更要说这是磁场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一种文学的力量;这种力量,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一种友谊的升华。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