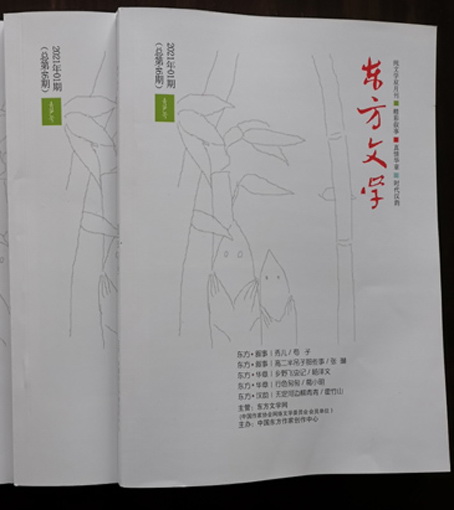江子这些年致力于散文书写的变革,前两年陆续读他的“乡村纪事”系列,对他的写作或多或少有了些了解。近日收到他寄来的《苍山如海》一书,本来打算抽空翻一翻,读了两篇,却有些放不下了。
《苍山如海》系列散文写的是上个世纪与井冈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其中一半的人和事只存在于口传和片言只语的记载当中,并无详细的历史档案。要把这样一个个人写活,至少可感,并非易事。江子抓住了一点,就像抓住了风筝的放线摇柄——那就是山,井冈山,人物与山成为了一体,事件与山成为了一体,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山成为了一体。我将其分为3种形式:由物达人,再至山;由人达人,再至山;由行为(或事件)达人,再至山。换句话说,没有这座山就不会有这群人,而没有这群人,这座山就失去了灵魂,也就失去了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严格意义上,历史是无法还原的,文学书写中的历史,更多的是运用我们的经验,从人的行为举动上判断其价值,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苍山如海》如是专写细节,写透细节,写准细节,写活细节,从不同的角度、视野让细节展现出生机与魅力,却又在细节的边缘戛然而止。《苍山如海》总共17篇,每一篇并不长,往往是从一个很细微的地方入手,写到遐想将至的地方则果断收笔。
《苍山如海》中的《信》通过革命恋人的书信直观地将特殊时代的情感表达写得真挚而动人,毫无夸饰,亦无需点缀,那几封信,尤其是最后那封“无字”的信,直击我的内心。《母亲》可以说是资料较为翔实的一篇,因为其中的主人公陈正人1959年还在妻子陪同下回山里祭拜了母亲。“有一种建筑,比任何房子都要坚固,它的名字叫做母亲。”江子的叙述简约而有力。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母亲而言,她或许不知道儿子的“理想”为何,但她有为儿子承担巨大痛苦的能量,这应该是人性的力量吧。《拾镯记》的小巧灵动也是我很喜欢的,它似乎运用了小说的叙事手法,却又不失散文的淳厚,王佐、袁文才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的特殊人物,在江子笔下从容而具体地得到描绘。一只镯子,犹如一个带着体温的符号,让人物背后的大山显示出了雄浑与敦厚。凡此种种,不用一一赘述。
散文的变革是一篇一章渐而做实的,江子兄的努力显而易见,那就是贴近再贴近读者,用心靠近他们;简略再简略文字,用感情取代说教。井冈山是篇大文章,非常之大,写的人很多,但能被读者记住的却不多,唯如此可见江子之良苦用心。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