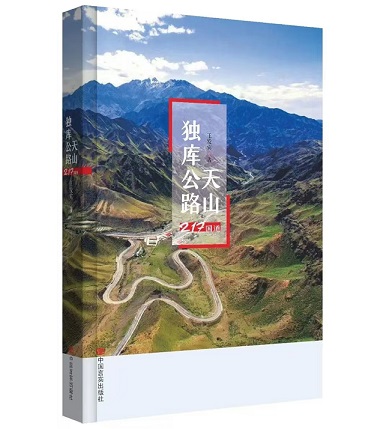作者方平,又名方平直。1963年3月生,浙江舟山人,著有长篇小说《奇花》。
【内容简介】
在他的故乡,他的昨日,时光渐行渐远,万物愈灵愈美。
那些远去的吃食,年糕、芥菜、酒酿;那些久违的鸟兽,梁上燕、村狗;那些消逝的人事,木匠、酒徒、和尚;那些漫漶的时光,午后、暮色、春雨;那些生锈的地方,寒溪、池塘、漏屋……在时光照耀后都有一种惊人的美,连晒太阳、闲坐回首起来都那么勾魂摄魄。
花如掌灯说荒村景物、人事以及物是人非,追忆流年,随想故旧,心似丝,文如苔,织成岁月的绿毯,这里是另一种深思,是安静的田园,亦是悠远的古典,再不落笔就忘了。
他安静,我们喧嚣。而为什么他闲敲棋子,却正好打在你我心头?
- 序
这个尚未炎热的初夏,让人不解的是,一部《舌尖上的中国》竟然火起来了。
在第二集《主食的故事》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浙江慈城,有一对空巢老人,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就是儿孙从宁波回来时为他们制作可口的年糕。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年糕唠着家常,其乐融融。然而,短暂的团聚之后,儿孙们各自开车离去,家里又剩下这对老人。
一部关于吃的纪录片,在中国能火,很难,除非是能讲出来吃背后的人生况味。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冬天北京餐馆里的鱼头泡饼,鱼头来自千里之外冰天雪地的吉林查干湖,是鱼把头凭经验、眼光和运气在冰层下布网所得;而高档餐厅里稍煎就香气四溢的松茸,则是云南香格里拉的小姑娘背着篓子走一公里才能采到。得之不易,炊之不易。
对中国人来说,对吃最在行,桂林的米粉,岐山的哨子面,关于吃的记忆,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故乡的记忆,一方水土一方吃食,即使离家万里,我们想念的还是老家的街边菜。
据说战时白崇禧在南京,想吃米粉了,都要从桂林空运卤水来,因为味道正。
可见,味觉的记忆之深,如风入骨,是世世代代的游子们骨子里散不尽的乡愁。人生水远山长,止戈为武还要靠故乡,能冲淡硝烟的一定是炊烟,能驱散乡愁的一定是乡音。
花如掌灯的这本《故乡有灵》,开篇也即是说吃,年糕、鱼羹、蚕豆、酒酿,他也是浙江人,生于舟山长于舟山,有山,又靠海,吃食与我们内地不大一样,我家那里无山无水更无海,能吃的都是土里长出来的,地腥味;而他,则是一吞一咽之间都有山与海的记忆。
我听人说,小时候一起吃大的伙伴,到老了会有一些相似的习惯和动作,不知道真假,但是我有时候想,童年时一起吃大长大的人,多少年后若再相见,会有一番怎样的对白?
王安石的诗,三十六陂春水,白头相见江南。那么相见之时,我相信两个鬓毛衰的老头子,谈论的一定是小时候在哪条河里捉鱼摸虾,当年谁偷了六一公公地里的蚕豆,两个人谈笑之间,会取笑当年的对方,会感慨世事的白云苍狗,到最后,各人眼中都饱含一滴泪。
在那滴眼泪里,有一发青山,有家国记忆,还有少小离乡时一路上的烟云。
《召南》里说,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这白茅,花如掌灯的乡下有,我家乡下也有,小时候馋甜,大了馋咸,我童年就经常在田垄间挖了吃,味道微甜,今天的乡下白茅许是不多见了,即使有,也不见得有人挖了,刻意去挖,心意也不再对。
所以读《诗经》,我念字如嚼,一边嚼出白茅的甜味,一边嚼出回不去的酸味。
我有时候看《诗经》,并不单单是为文学,而是想重温那个水远山长的田园时代,今天农业成了一种弱势,耕不足为业,更不见农业时代的简静美学,人心周围砌满了水泥墙。
我小时候,乡下还多是泥土墙,怕贼人爬墙入家,很多人家都在墙上种了仙人掌,仙人掌每年开花,结果要四年一次。我有一次,看见邻家墙头的仙人掌结了果,就想方设法用树枝扒拉下来,捡了就赶快逃,结果手上被扎很多小刺,却并不痛,只是一根根要拔很久。
仙人掌的果实,是酸甜的,但是不敢用力吃,虽然没有刺了,依旧还是怕被扎。
我虽然多次被刺扎过,但却不曾被人生所扎。所以花如掌灯说,从来认为男人白晰,是件羞耻的事情,我也有同感,而且我至今亦白,大抵是不近烟火,不懂人生愁苦故。
但惟是这样的白面书生,才最适合做游子,少小离家,一路学书学剑,文武艺要么货与帝王,要么卖给富商大贾,一世为稻粱,为前程,为前程也是为稻粱。鸟为财死,人为食亡,外面的一碗饭也不好吃,甚至为了一碗饭,心蒙尘,眼蒙纱,但见财路不见人路。
我向来不喜欢在城里的日子,但为生计计,亦无他法。城里的日子,是社会,是日期;村里的日子,是光阴,是人世。进城走了几十年,我们学会了吃大餐,学会了盘桓人脉,学会了心计和旅行,但却丧失了对食物的记忆,对亲情的记忆,对快乐和简单的记忆。
故乡的那一抹炊烟,在工商时代的欲望和消费中,越飘越远,越飘越淡••••••
人世越走越远,却越走越小,气魄越来越小,格局越来越小,性情越来越小。
到今天,我还在怀念幼时在箱底闻到的、放久了的苹果味,以前家里穷,苹果也不常吃,父母怕偷吃要藏在箱底,等拿出来,连同放一起的布匹,一叠一叠都是香味,都是岁月;而头天刚磨下来的面,闻来也是香的,白天晒好的被子睡一夜醒来,还能嗅到风与阳光。
虽然南来北往好些年,我仍然在城市里待不习惯,楼高了不接地气,树不绿没有生气,邻里不通没有人世,唯有枯坐家中,看着窗外一群盘旋的燕子,才找回一点生机与岁月。
这燕子,是从旧时王谢家飞来的吧,飞过杜甫的草堂,今朝落在这闹市歇歇脚。
所以我在城里,远观而不亵玩,只是遥看车如流水马如龙。不出门,家里就是我的村;出了门,繁花都是别人的城。不得已时,才出去走一遭,且当红尘中人完成红尘中事。
花如掌灯说,他至今还有情不自禁坐地的习惯,是在故乡时不知不觉落下的动作。
今天在城里,他偶尔也会在闹市这样呆坐,坐得与旧日无异,不过蚂蚁变成了人流。而这人流如织,却不再有他舅公那样的人物,四邻八乡都闻名,“凌厉有智慧,作派蛮横,读过《三国演义》,村里人有造孽打架或者婚丧红白事都会来请他,是压得住人的人物”。
城里呆久了,我也不觉会怀念少时村里人物,抬棺材的把头、做家具的木匠、婚丧嫁娶的总管,都让人在岁月中亲近,即使二流子、痴呆儿,也都比今人有模有样有倜傥。
及夜半闻邻女夜织,机杼声声,也会让人出一种坚定,一种永恒。
我的大舅,地主人家出身,过过优渥生活,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堂里做过学生,解放后因为成分,一直赋闲在家,激动时候手舞足蹈,人称“胡疯子”,其实他不疯。他与我谈文学历史,写毛笔字给我看,真是铁画银钩,撇捺人间,每一个字都锤进了昨世今日的分量。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我非为大舅叫屈,而是爱这草泽,爱乡间容他的好意。
而且我的故乡,也有金银花、兰草、苦楝树,也有村狗、麻雀、梁上燕,也有鬼有乞丐有和尚,这些今天城市人都不大能见到了吧?儒家讲,做人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我觉得,惟是在这样的乡土中浸润过,知物力维艰,懂人情练达,人生才能豁达而真实吧?
即使是离家万里,你长大之后的每一寸人性,也都通达着小时候的每一寸物性!
胡兰成年轻时,去北京谋生路,一路上渡长江,济淮水,望泰山,过黄河,此地古来出过多少帝王,但他在火车上想,即便是下来在凤阳、淮阴或徐州、济南,做个街坊小户人家,只过着今天的日子,亦无有不好。因为他也是个本色之人,通晓乡间民意的好。
他的老家在嵊州,绍兴下面的一个县,与花如掌灯的舟山相距不到四百里,《今生今世》里的浙江乡下,日是日,月是月,江河都有情义,纵使村夫村妇世界,也亮堂斯文到豪华。
浙江更还有鲁迅和周作人的乡下,郁达夫的乡下,蟋蟀声声,春草池塘。
江南的乡间草长莺飞,杂树生花,是最好的乡村世界,村中一日,世上千年。
在这样的江南,铁马冰河我或不爱,金戈铁戟我或不愿侍弄,不当英雄做个小民,纵被骂作是温柔乡里做道场,但挈妇将雏,柴米油盐,做个江南村里的小户人家,躬耕富阳,日出日落,闲时卤水点豆腐,枯坐看蚂蚁搬家,忙时割稻插秧,也是人世的至大滋味吧!
哪天有人闯进来,一搭腔,即使被说作“无论魏晋,乃不知有汉”,想来也不错。
花如掌灯的《故乡有灵》,我是当成一本《出埃及记》来读的,作为一个个进了城的农家子弟,我们走出了三个故乡,地理上的故乡,岁月上的故乡,心灵上的故乡。今天,故乡比斜阳更残,那年那月那地怕是再也回不去了,只有躬耕纸上,在字句间重觅往事历历吧。
以色列人出埃及,是为躲避压迫寻找光明,而我们出故乡,是为了从一个光明寻找另一个光明。以色列人历尽千险万难终遇救赎,我们从故乡走到他乡,却一路跌跌撞撞。
中国人没有耶和华,故乡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丢了故乡的人,也就永远走不进天堂。今天,我们走出土地,走出故乡,却也把土地和故乡赋予我们的秉性,丢在进城时的路上,付与日月,还给山海,但我们越丢越不快乐,越丢越比来的时候恐慌。
这让我怀念起炊烟和大地。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在这个浮华到坚硬的年代,还是回到心中的那个故乡吧,慢三拍,静一生,听听平时听不见的山幽鸟鸣,看看寸寸光阴在庭前徘徊,回去见见当年偷瓜被他逮住痛打的那个邻居,闻闻麦香和瓜秧,吃青菜,喝白水,静听岁月的拔节与忧伤,这才是人世的大信大爱。
所以,你问我为何在城中不语,其实我是在怀念当初离家时的暮色照大地!
是为序!



 您的位置:
您的位置: